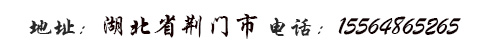姜宇清诗选这乡土里的桔黄的潜艇潜在我
|
姜宇清诗选 一只西葫芦瓜 一只西葫芦瓜,置放窗台上 这乡土里的 桔黄的潜艇 潜在我视线深处 这么久 它的成色 是黄昏的雕像 老稠了的阳光 和成的泥巴 现在它不那么普通了 一只西葫芦瓜 我不好随意打开它 它是一个宇宙的模型 浑沌未开的形状 裹了陨石的裂片,包了大气的瓤…… 地头上的鞋子 到田里去,显眼的是落在地头上的一双鞋子 很多的地头上都有一双这样的鞋子 说不上款式,新潮,大多是家做的大多是旧鞋 孤独的鞋子安静的鞋子停下来思考的鞋子 是地道的农民的鞋子,丈量土地的尺码 脚软肉嫩的都与它隔着一层 它适合放到耳朵上听听,鞋口真大 如举起的一只巨大的海螺,听到什么呢 阳光、雨水,黄昏里泥巴与草籽的气味,一鞋的风流 主人还远在天边 黑条绒的鞋子上浓缩了黝黑的垅行 蓝布的鞋子与天空,淖水一色 鞋子有着鞋子的派头或风度,在不远处 有一双白色的鞋子,新寡的鞋子 正是一对白鸟,似卧,似立,似飞,似翘首远望…… 数学启蒙 识数时,母亲出了第一道算题 “三猫六兔九公鸡七十二只狐狸几条腿” 开始演算,我用十个手指 十个手指不够又搬动十个脚趾 十个脚趾不足 又搭上地上的缸,墙上的草帽,院里的犁铧 那时不懂再添“两个黄鹂”“一行白鹭” “七八个星天”“两三点雨山” 满月的夜晚,母亲出了第二道算题 “十斤的油篓七斤的罐三斤的葫芦瓢分一半” 母亲的题有了难度 我竟容易地做好了,母亲亲了我的脸 母亲说,数有分合数有兆谛 那时的我还不足去深追 以后倒是常喜欢吟味类似的句意 诸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棋手 开春的一场大雪为他铺开棋盘 还未落子,心中已有了赢的兆头 排局布阵,楚河汉界一路撕杀下去 就到了中盘,如日子已进入夏季 麦田很好,草木很好,绿油油的棋的走势很好 但他还是不敢声张不好预测 月亮晃在窗格,举棋不定 对面看不见与他走棋的那个人的面孔 不知道他又会使出什么招法 也许它一变脸就蛋(冰雹)打一条线 也许它一发怒就洪水淹过半 那时就只有收拾残局,不,是走好残局 如扶起几株还未倒下的谷子,支起几颗 命大的高粱,他一边叹息着,中盘弃子太多了 地下的果实是他手中摸得发热的暗子 整盘棋的大势,他还控制着 他的秋天的棋锋毕竟凌厉 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毕竟是王者之气 早晨,大雪的棋面上,他先捏起一子红日 将了那对手一军,成为绝杀 下种 一片瓜子埋进土里 一粒红豆埋进土里 这都是下种 一阵风状的根须埋进土里 一束闪电的蚯蚓埋进土里 这都是下种 一点陨石的痣埋进土里 一块钝剑的疤埋进土里 这都是下种 一枚发光的舍利埋进土里 一册发黄的文字埋进土里 这都是下种…… 村里有的人死了 装进棺材 也埋进土里 死了的没有事情了 活着的悲伤着 那时,我也就觉着是在下种 好比那片瓜子那粒红豆 好比那枚玉那册字 好比那点痣那块疤 好比那阵风那束电…… 它们都不见了 它们都没有了 它们都变了形 从土地里冒出来 比如我看见满街的小孩子乱跑 都是新的,都是破土而出的 打草 闪电在云层间闪动,大镰在草莽中闪动 大镰带着风来了,黝黑的草里来了电 大镰的风弹上去叮叮地响 镰刀对麦子要躬下身去,大镰只直了腰杆与草接触 深秋,在奔雷中看厚重的天页下父亲打草的姿势 他以镰杆为半径以自己为圆心 草的时空有了刻度,大镰为一春一夏的雨水收官 所有的草为大镰倒伏,所有的秘密为大镰打开 我一直不认为大镰是刀,大镰是床,草的床 它将草原裁成若干几何形状,让草休眠 草籽在父辈掌心里一闪,四时完成了过度 雨前 鸟雀都不见了,高天上的鹞子 滑翔着,浓黑得是沉重的云块 雨前,坡岗与淖水都阴森森地亮着 雷电呼应中,村庄总是紧张和激动 这时,我看见大花大花的长蛇了 它昂着头颅,高竖着锦绣的胸脯 大摇大摆通过乡村大道 沉默的运行呀漂亮的阴冷呀 雷声拥着它没入密集的草丛,闪电照耀着它 杂花努力掩盖着它诱人的身段 草梢是弯弯曲曲地流动了 是花色的风是花蛇的风…… 鹌鹑的叫声 他们最喜欢听的不是夜莺的叫声黄鹂的叫声 他们最喜欢的还是鹌鹑的叫声,其次是百灵的叫声 鹌鹑叫第一声,麦子黄第一垄 鹌鹑叫了第二声,麦子黄了七、八垄 鹌鹑叫第三声,就黄了所有的麦垄 还有要收割的黄了的梦想的神经…… 也有黄不到的地方,夏夜,野苜蓿花 把月亮染成紫面门神 疯长的苜蓿地里也疯长最原始的图腾 鹌鹑不叫,偶尔有猫头鹰被旋转到一定角度的笑声 回到鹌鹑土黄色的叫声里 在土地成熟的色调中劳作的男人和女人 在一垄一垄地写诗 他们写的是草律,粗粗拉拉,方方正正 云中的百灵是平声 忽然从脚下或镰刃上从容起飞的鹌鹑,是仄声…… 老虎一面 日头有没有毛,脚,嘴巴和肚子 日头的线路,这都是小时候的问题 我爬上山顶去迎接日头 我面前隆起的是毛茸茸的日头—— 我的手已放上最高的岩面 它的两只前爪也分明搭在岩面上 我和它面对面 我从山之阳它从山之阴 鼻子的鞘垂直而下 胡子的剑光芒四射 毛色的流水静静响着 嘴巴的疆土厚厚关着 光源色 自然的光源色 大调子 宇宙的大调子…… 后来,我们擦身过去,各走各的路 我不敢回头,不知它回头看我没有 峰巅的积雪红了 果子,干花,枯叶渐渐红了 山谷里林表里幽草里,有巨大的回声…… 回家,我没有与母亲说起这件事情 半年后我与母亲提起过有这么件事情 母亲说,他是有来头的, 母亲还历数过许多虎星下凡的人 当然母亲那次没有再带我去井口,叫魂…… 马群嘶鸣 响骨在敲,鼓点飞动,不打结的河流,没有顿号的长风 云鞍的白玉,奔突的气韵,风云拉开的卷轴的心 曦光的紫气,暮色的香尘,远古神话中一块飞毯的掠影 节奏浇铸的时空,汉字燃烧的象形,马尾扫过的枯荣…… 嘶鸣的长河而下,注洪荒以血,赋天地以神 根本就停不下来,仔细地听仔细地听,瘦瘦的乡村膘肥的意境…… 一个姿势 他不会如城里人,习惯地把手插入衣袋 或身的两侧,钟摆似的, 不拿着农具,不干着活计,他的手就没处搁了 他就淡淡笑着背抄着手朝前走着 这个姿势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生下来就从祖上从父辈那里继承的 也可说是胎里带来 庄稼人很多的走法就是这个姿势 他们自己不觉得雷同,淡淡笑着背了手朝前走着 他们决不那么严肃那么心事重重那么沉重地走 背抄着手走着,是一连串辛勤动作中的 一个简单过度,是世上最劳累的人的一个闲笔 这个姿势看上去很洒脱 但不够华丽不具气势不具太多的梦幻色彩 这是一个很实在很轻松很从容的姿势 这是他们面对前面的生活的基本姿势 这是他们面对前面的苦难的基本姿势 青蛙 那一只肉感的颤动的绿 在古寺一侧,尤其是 那只老年的蛙,声音沧桑地绿 那一只不朽的木鱼 均不为所动,只是依旧地 与之和鸣,敲击 那一只在池塘,那一只在佛堂 那一只于城外,那一只于尘外 那一只将月点圆,那一只将经敲残 有欲的和鸣 无欲的敲击 一只棕红,一只暗绿 木鱼是木质的青蛙青蛙是肉质的的木鱼 诗人档案 姜宇清,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坝上人,曾两次在康保二中带实习生,曾在康保四台房作为教育支农工作队员与队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诗作多忆坝上草原,怀念以往岁月。现居宁波,供职于浙江万里学院。 扫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cs/13727.html
- 上一篇文章: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我党高层著名收藏家
- 下一篇文章: 西安发生一起凶杀案一男子被当街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