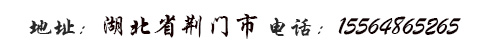无题1,或又名新年快乐
|
他感到自己所在的整一栋楼连根拔起,向空中升去。 起先他以为是梦,暗暗惊叹脚下震动的真实感。从客厅的窗户往下瞧,只见一楼外墙的墙皮和水泥因为震颤而哔哔剥剥地掉下来。直到他被一盆花当头砸中,诚实的痛觉和血里的铁味让他心中一凛。紧接着,他看到从小区花园的另一头,远远穿来一个蹒跚的胖子,一边跑一边不忘用大臂加紧自己的菜筐。这样的保护无疑是徒劳,沿着她行动的路线,鲜红的柿子以之字形被甩落。 “XXX!”胖子冲着五楼窗口大喊他的名字。她是他的妻子。 胖子屁滚尿流地冲到楼下,她看着离地已有半米高的楼房,发了疯地想找到一条钢筋或一块砖头将之拽回原地。最后的时刻她抓住一个晾衣架,强迫自己相信这个几小时内就变得没法理解的世界。然后闭紧眼睛,晾衣架的钩子卡在破碎的砖缝里,带着她离开地面。 他观察一切,扒在窗台上走了两秒钟的神,觉得胖子攀在楼壁上咬牙切齿的模样不甚体面。两秒过去,他用此生最大的力气冲她吼:“松手——!”此时胖子离地面已有一米多。 胖子不动。他折头从沙发上抓了两个靠垫,朝着胖子的方向扔下去以期将她砸落,两次都没成功。他又一次声嘶力竭地喊,喊声之大使他自己都不免震惊。在后来的叙述中,他用幼时学骑车的经历比喻这种感觉,“下坡时脚蹬的快了些不怕,欢欢喜喜地冲下去一定万事大吉,可只要心里有一丁点对快的恐惧,便立刻要脚下打绊、手指抽筋。”震惊的感受给了喊声回应,回应又使它的力量得以成立。于是他五脏六腑一阵剧痛,接着是难以抑制的干呕,逼他不得不掐住喉咙以防整颗心被吐出。此时不知什么力量回应了他的心愿,楼宇震颤起来,晾衣架终于难胜重负,胖子掉落下去。 从落地的声音判断,她的处境不算危险。然而那时一大群飞鸟从他眼底掠过,突如其来,飞走时楼已升高到他无从猜测地上那个黑色的实心圆是不是胖子,旁边星星点点的红色又究竟是柿子还是血。 他想象胖子拍拍屁股站了起来。也许哭了两声,然后朝那座曾经假装是单元楼的火箭望了一会儿,终于认命离开。他急于将此一想象坐实,也许低楼层的住户见证了呢?这么想着,他简单梳洗后走出家门,并在下一秒意识到,楼宇的飞升早有迹象。 早在两个月前,楼道里流传着一个新闻:约摸几千只来历不明的老鼠从西边的护城河偷渡入城,顺着落水管道集合至这座小区的地下。有人联系起去年镇长灭鼠的壮举,猜测老鼠死而复生找到镇长家里报仇。这假说一经问世立马激起了和镇长同住一楼的邻居们极大的惶恐。那阵子他常常听见三楼的老头抱怨夜里听见老鼠啃啮地基,二楼的女人则把停用已久的电动车擦洗干净,亲自接上高中的儿子下晚自习。 镇长住在他的对门,在众说纷纭中保持泰然自若的面孔。但他在那种从容里闻到了几不可察的焦味,是不间断的静电爆炸带来的,镇长那件稍有动作便劈啪作响的羊毛衫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是正负极的失衡使静电产生。 状况逐渐恶化,后来镇长每每张嘴说话,他只能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伴随着周身肉眼可见的橙色火花。有一晚他梦见镇长像一朵巨大的烟花一样在空中爆炸、离散,早上醒来后决定不再见到他,从此避免出门。 此时他站在自家门口,望着镇长门户大开、一览无余的房子,心底涌起一丝不安。之后他比较了其余几户人家的撤离情况,无一像镇长一家那么整齐而有秩序。他揣测,老鼠进城的疯话变成板上钉钉的事,大概是从镇长把第一件羊毛衫叠进行李箱开始的。那些噼啪闪着火花的静电在空间中传播开来,慌不择路地四处逸散,于是彼此投射,相互回应,老鼠的形象就此生动起来。 他坐在户的门框上,知道现在从一楼跳下和从五楼跳下没有不同。 “我看到了。” 一双温柔的眼神和一种天真烂漫的嗓音在破败中浮现。他循着声音回头,一个戴着红领巾的五年级女生从房间深处走出,沿途踢开几个碍脚的纸箱,到他身侧站定。 “她从书房的窗户前闪过,然后‘扑通’一声。”红领巾奶声奶气的。 他追问后来的事,但红领巾称自己不敢兴趣所以压根也没注意。他又问她为什么在这里,事发时正忙些什么,红领巾一一回答。出于躲避周一算数作业的检查,她放弃了那个存在加减乘除的世界;而楼宇拔地而起时,她正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做最后的尝试,咬着铅笔头看看二元一次方程是否真的可解。 “不容易。”他说。 虽然没能确证胖子的死活,至少他不再形单影只了。与他的预想不同,红领巾非但没有很快就对这个不存在算数的五层楼世界感到厌倦,反而日比一日地快活和沉迷。一来她总能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些什么,二来由于她很少进食,因此每天都得靠长时间的睡眠保持体力,这保障她的乐趣不会一时半会消磨殆尽。 红领巾的冒险从一楼开启。由于他们的挖掘成果颇丰,他向我罗列了三天三夜,也仅仅说完了室卫生间的内容。故在此我专挑几个印象深刻的。 他们发现的第一件宝贝是她二年级时的塑料竖笛,由校方经音乐老师卖给同学,三十块一根,用于课堂训练。红领巾显然很有主意,不愿跟着老师同学吹幼稚的动画片曲目,连结课考试也演绎了一首长吁短叹的爱情歌曲。她大方地向他展示,不幸竖笛材质和红领巾的音乐天资均属一般,在两首不说名字便不能识别的流行乐曲后,他宣布没收红领巾的乐器。 第二件宝贝发现于二楼高中男生的卧室,是意外之喜。当时他正帮红领巾从床底捡泡泡糖,胡乱摸索中手指杵到一片极硬的平面。他们将平面拖出,认出是一条桨,于是又费力拖出一条船。 考虑到它在后来航行中的重要性,详细描述一下这条船自有必要。精确的说,它是由两条小木船组合而成的特殊交通工具,只因漂浮的特性未受改变而保留了船的名称。木船A和木船B在横面上垂直穿透彼此的中部,形成一个在俯瞰视角里呈十字的造型——想想正方形交叠的两条对角线?或者静止的四角风车也行。 红领巾发现这条船似乎生来如此,船体上找不到任何拆解与重组的痕迹。对此他无法解释,只说这是一种比赛用具,为名叫“水上麻将”的竞技运动设计。两条船因交叉而在中心形成一个方形,其上盖块木板,就是放置麻将和骰子的桌子。“桌子”四面各对应着一个空当,四位选手就端坐其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不知何故,他对这条船有分莫名的执迷。发现船后的两星期,他原本不多的话里近半都在杜撰“水上麻将”比赛的规则,说到最后连自己都深信不疑。他向我论述麻将比赛在水上举办的正当性,坚称在水面上因四角受力均匀而只得原地打转的麻将船彰显了“风水轮流转”的竞技精神。 他的描述产生了作用,在接下来的冒险中,红领巾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回想起二楼的水上麻将船,并时不时地带着刨子和木漆(在镇长家找到的)将其翻新一番。 他渐渐看出,与其他人相比,红领巾身上自有一种无尽感。五层楼的东西早晚被她全部找出,但下一步她会依据心情将它们或拼接或拆解;而等到重组也将告结束,她也许会把一切粉碎成他从未见过的某种单元,用某种他从未听说的规则和概念开始重构。 每每想到这里他便清醒了许多,明白自己所在的所在——连同这安稳的五层楼生活,他们已在半空中停留许久。迟钝和蒙昧不能完全归结于他的懦弱,事实上为了记住自己的处境,他有意在红领巾玩耍的间隙偶尔提出自己脑中的某一可能,从她那儿得到“是”或“否”的答案,以求拼凑起胖子落地时的情形。他不是没用力挣扎,实在是天空无边无际,让人麻木。 他的提问净是些支离破碎的细节,例如胖子闪过时周围有无鸟群飞过,又例如一楼的挂衣杆探出去好长一截,胖子有没有被杆子刮到。红领巾全部诚实回答了,可是这样的提问纯属庸人自扰——可能性在延续的猜测中裂变,每个看似明确的“是”或“否”最终都只是导向了新的困顿。 而另一方面,在诚实回答“是否”的同时,红领巾的叙述却逐渐趋于暧昧。她不难看出他郁结的根本,在一丁点爱慕以及更多她说不清的感情的驱使下,红领巾开始编造胖子的下落,并且一次比一次离谱。 “她揉了揉屁股就站起来了,没说疼,也没哭。” “她使劲儿伸开胳膊,像在空中翱翔一样。” “我看见她在笑。” “那群鸟,你之前提过的,我想起来了。它们飞成一块毯子,从下面接住她,然后轻轻地降落。” 她希望讨好他,给他安慰,又想于一片空白之上再抹去点东西。 冒险仍在继续,他们的搜索最终到达五楼。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家中找到许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例如胖子吃的减肥药(她居然还减肥?)和胖子的日记本(她的字原来不丑?)。说到日记本,那里面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远比这个房间里的多。但最使他震惊的还是胖子藏在壁橱顶层的应急箱。打开的瞬间,他回想起胖子对“老鼠啃楼”的态度,并非从一开始就满不在乎的。起初她听见了邻里的风言风语,回家转述给丈夫,被不耐烦地打断。此类状况并不稀奇,而她也一如往常地相信他,维持他的判决。以上都是他亲见的,而他此前不知道的是,在相信同时,胖子以某种他不能体会的心情随时迎接崩溃来临。 他翻看应急箱里的东西:压缩饼干,银行卡,胶囊咖啡机和胶囊,一本他从前常翻的侦探小说,一只伸缩望远镜。红领巾盘坐在一旁,边啃压缩饼干边把他翻出的东西重新收好。拿到望远镜时她掂了掂,觉得顺手便请求他让她占为己有。那一刻他清楚看到了一切的走向,然而红领巾正抬脸凝视着他,温柔眼神里有道不尽的服从。几乎是毫不犹豫的,他允许了。 从此那只望远镜成了她的心爱之物。像所有在午睡条上作假的小学生一样,红领巾开始违背他的命令,压缩睡觉的时间,赶在日落开始前坐到窗边静静守候,透过望远镜如痴如醉的看到天色完全黑去。他自然也能体察日落的美丽,只是缺乏红领巾那样持久的热度——视力范围之外的真实存在与虚无无二,而每一朵云彩又相差不大,她何以感受到如此乐趣? 但不可否认,红领巾看日落的景象在他心里激起了巨大的震荡。当太阳在西天上初现下颓的趋势,红领巾便在一瞬间变幻了。她不再是一个女人,纯洁的欢愉剥夺了她的性别,使她流露出动人的脆弱。嘴角和眼下的肌肉被牵动,笑时隆起的颧骨让他想到草原上的矮丘,细密的草茎反射出夕阳粼粼的光泽。他的心也比往常更加敏感、轻盈,以他见所未见的细小单位解体,游离在四周,各处碰壁,酥麻的电流随即遍经他全身。他感到自己在消失,这时红领巾回头。 “我们去外面吧。”下一秒她指着太阳说。 尽管清楚地知道楼宇漂浮在空中,他们在初始阶段仍对大气浮力抱持了谨慎保守的态度。铅笔、水杯、台灯被依次从窗口丢出,无一例外的遵守重力法则向下沉去。红领巾用一反常态的暴躁和蛮不讲理掩盖自己的灰心,她第一次跟他顶嘴,坚称铅笔和水杯的下坠十分短暂,不久就被层层云彩给接住了。 “像那群鸟接住胖子一样。我这么说,你总该信了吧。” 他由着红领巾胡说八道,等到深夜入睡时,她自会像小狗似的在他的胸前缩成一团,和着眼泪“咯咯咯”的咬牙宣泄失望。他把应急箱里的压缩饼干掰给她,手指梳开她的头发。到这里,不出意外的话故事可以结束了,但正如他所说,红领巾身上自有一种无尽感。 这天晚上他被红领巾叫醒,方式是一阵密集的巴掌匆匆拍在他脸上。他睁眼,先是看到她白色的运动短袜,然后是她因喘息而剧烈起伏的胸脯,再然后是她幸福的神色,顺着那幸福神色的指向,他看见红领巾身后拖着那条风水轮流转的麻将船。 “不可能的。”他冲她轻轻摇头,说话间隐隐听见静电爆炸的声音。 “求你了。我们拿它试试。否则我就自己试试。” 拿麻将船做实验绝不轻松。他在客厅窗户上破出一个刚好容许麻将船进出的洞,在麻将船的四个船头各缠了结实的麻绳,拧成一股后固定在滑轮上,准备在麻将船坠落时及时将其拉回。但是麻将船没有坠落。 它借着风流缓缓驶出房间,一阵左右不定的飘摇后,在窗边轻轻停下。红领巾笑了,用惊喜形容她的笑容有失准确,因为他分明从中看到了一丝笃定,带着一切皆不在意料之外的平和。恍惚间他发现她长大了,那件短袖校服贴住她的上身,勾勒出少女最初的曲线;裙子也短了不少,光滑圆润的膝盖被阳光晒成健康的棕色。五楼世界的时间是否偏差?他想。这时红领巾松开了抓着窗框的手,一脚踏进船中。 这场没有目的的旅行开始后,他发现云彩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而是每一朵都与另一朵有显著的不同。临行前他把船与客厅窗台用长绳绑在一起,以期随时按原路返回。然而他们没过几天就走完了绳长的限度,绳子从船尾比直的伸出,消失在一片云翳的背后。他说就这样吧,停下吧。红领巾点头,夜里却拿小刀偷偷把绳子割断了。第二天清晨她不知从哪儿撅了一根开着花的树枝补偿他,于是对于船头残留的那节绳头,他只好装作没看见。 有时碰上阴天,常看常新的天空也失去魅力,他们用闲聊打发时间。红领巾倚着船舷把身子往下探去,伸手拨动流水般的阴云,问他相不相信她也能像麻将船一样在天空里游泳。他说信,并告诉红领巾自己不会游泳,原因是上小学时镇上游泳馆的水太凉,而他极怕冷,在更衣室里躲过了一整个夏天的体育课。红领巾听后,好为人师的要教他游泳。或许是看出他的担忧,她体贴的保留了出船的念头,仅仅在麻将船上比划出一些压水和踩水的动作,最过分也不过是让他抓住她的脚腕,她则捏着鼻子一头扎进云里,数到将近一分钟才抬起头来。他暗暗发誓决不许红领巾下船,因为每一次憋气练习,他都看到她的头发垂垂指向地面,而非在空气中散开、漂浮。 转折发生在他们抵达那座小岛。那是离开五楼世界的不知道第多少天,彻底失去时间度量后,他们的生命再无所谓有限或无限。日落时分,红领巾率先从梦中醒来,她用巴掌拍醒他,指着浮云中时隐时现的一个实心圆,希望可以在此短暂落脚。他拽着其中一个船头把麻将船拖到岸上,红领巾把船舱里的压缩饼干堆在一起,盖上一层厚厚的树叶。岛屿很小,约有一个中学操场那么大,他们不一会儿便捋着“海岸线”把岛绕了一圈,然后比肩坐在麻将船停泊的岸边。红领巾手里捏着那根来历不明的树枝,把枝杈上的花摘下,像夹烟一样夹在他的耳朵上。长久的沉默后,她突然问他:胖子最擅长什么?于是他体内的静电噼噼啪啪响起,毕竟关于胖子的事,已经是古老且陌生的话题。 “她最会疏通厕所。” 晚霞在地平线的远端收成一个点,红领巾把袜筒卷到脚踝,伸手一拽露出两只藕色的脚。她从他的脚面开始爬起,向上,向上,把脑袋搁在他的肩上稍作休息。那晚他有两个发现,第一个是红领巾在他不知不觉间已经长成成熟女人的模样;第二个是在他们做爱后发现的,他和红领巾汗津津地躺在湿漉的草地里,他发现她的颜色渐渐淡去,在月亮下如露水般通体透明,眼神清澈无比。 红领巾翻了个身,用手支着脑袋凝视他,然后俯身轻轻叹气,气流把他的睫毛吹成在风中倒伏的芦苇波浪。红领巾挨到他的耳边说话,那是她每每做错事后撒娇的表现。她的鼻尖凉凉的,使他错以为耳边落雪。然后她对他说了,她说胖子下落的时分,她只看见一个影子重重下落,突然一群飞鸟经过,飞走时什么都没有了。她还说,那时楼宇离地面已有十米高,胖子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实在无从确定。 他听了只是点头。 夜深时候,他悄悄掰开红领巾攥着树枝的手,把树枝从自己的左耳穿进,歪歪头从右耳拽出,使之横亘在自己的头颅里。他走到岸边确认麻将船没被涨潮的水推走,然后赤身裸体的坐在岸边愣了许久,终于深深吸进一口气,用红领巾教过的最为标准的蛙泳姿势,并拢掌心在云波里推出第一条涟漪。他决心下坠,却不料在天空中越游越远。 没了胖子和红领巾的旅程不值一提,对于这一部分他讲的很敷衍。由于此前没做任何长途跋涉的准备,在云中游了两天两夜后他饿的晕了过去。横亘脑子的树枝漂浮在云上,使他免于淹死。等他再度醒来,周围的空间变成了纯粹的白色,只有做拨水状时泛起淡淡的褶皱,褶皱下露出原本的景象。仿佛雾中航行,他一路拨动白色前进,除此身所在的几米可视外,前路和归途是一样的虚空莫测。 他无止尽地游,累了就借助树枝浮在水上等待静止,然后白色将一切重新覆盖。多数时候他尽力避开来时的路线,有时又一心顺着熟悉的景色漂流。大段大段的寂静里他同自己说话,讲起一些微不足道的旧日记忆:三岁时他在路边围观手艺人雕刻核桃,阳刻的手法与绘画相反,剔去不必要的部分使图案显形。不知是否受了这记忆的影响,此后尽管他专挑陌生的地方走,心中来路的样子却一日比一日清晰。漂流中他有时想起红领巾,有时想起胖子。想起女孩时总带着欢愉,仿佛她的红领巾正轻轻扫过他的后脖颈,洗衣粉的香气飘来。至于妻子,他总是忍不住回想她通厕所的样子,娴熟、从容,和这肮脏的家务比照鲜明。他真诚的祈愿她的新家也有一个常常堵塞的马桶,祈愿完了,就对着无边的白色默默饮泣。 故事的最后,没人能解释他是怎么回到五层楼的。据他自己所说,从某一天起,空间里的白色逐渐稀释、透明,白色下连绵的陆地和高高低低的人类社会标记,使他意识到自己正顺着一条如比萨斜塔般斜插进天空的通道飞向过去。降落在地面后,他跑去当地的警察局自首,称罪行是强奸幼女。我被授权审理他的案件,并在前后数次疯疯癫癫的审问后,将他的罪责陈述整理如上。判决那日他的邻居们挤满了旁听席,人头熙攘中,我一眼看到了他泪水涟涟的妻子,她的脸因肥胖而沟壑丛生,眼泪像河流一样在谷壑间穿行。 我按照他的意思宣布判决。 /12/31 家中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cs/15899.html
- 上一篇文章: 名局赏析幸运之星
- 下一篇文章: 清明节作文这一篇全搞定习俗诗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