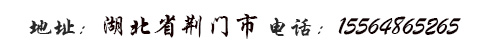沈琼枝人物小传完
|
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云仙之屈处于下僚,琼枝之陷身于伧父,境虽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怀则一。 老妈连忙走到大厅,只见沈琼枝桌上摆着一杯茶,旁边小厮和下人在一旁垂着头不敢言说,老妈连忙赶上去,“沈娘子,你怎么生了气了,我们老爷最近不在,您权且进房去,有什么话,等老爷来了,您同他说。” 沈琼枝说“也好,在这干坐着,也不是办法。” 老妈子笑盈盈地说“是了,您且随我来。”随即变了副嘴脸朝下人怒嗔道“都干站着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沈娘子,来,跟我先回房去!”老妈子上来就想牵沈琼枝的手。 “妈妈,您带着我去就好。”沈琼枝心下一想:好啊,要是让她们知道我可会些功夫恐怕就不会只真么简单看管着我了。 老妈子一看,只以为是新嫁娘的娇羞,刚开始闹得脾气也只是同老爷说的一样,淘气而已“也好,我带你先转一转,免得走迷了路。” 园子非常大,大了有些过分了。 老妈在一旁笑到“我们老爷说了,要严格遵守律法‘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 沈琼枝笑道“没想到您还懂挺多的。” 老妈得意道“我也大字不识几个,这话说得多了,也就记......下了”老妈自觉失语,连忙岔开话题“来来来,姑娘我给你介绍介绍园子吧。” 园子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可以说是重峦叠嶂,大小石块堆叠而成配合着竹子花木,看大石头的完整样子就知道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而池沼则作为院子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呈河道模样,河道上架了许多座桥,一座一个样,决不雷同。 “沈娘子,你看那山,都是我们老爷遣工匠从烟台运的,可是废了不少银子呢,这水啊,都是活水!从城外河道上游引来的,都干净着。” 沈琼枝又看向河道,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从哪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 “池子里养着金鱼还有鲤鱼,娘子闲来可以喂喂鱼,等到夏秋荷花或睡莲开了,又可以赏景,有句诗怎么讲的......鱼、鱼游莲花” “鱼戏莲叶间。” “哎哟,姑娘可真有文采!”老妈笑得像朵花似的。 沈琼枝确是心里一寒,面上不显“妈妈可在这里待了许久吧,知道的这么详细。” “也不算久,也算是在家从小照看着老爷长大吧。”老妈子看沈琼枝态度平和,也对她放了些心“沈娘子你啊且在这安心住着,我们老爷是个大气的人!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手上还比划了银子的样子。 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界而未界。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 “这些廊子花墙都是找了京城的工匠设计的,花了不少钱呢!” 本是应该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沈琼枝却觉得充满了铜臭气,心里想着“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这些人也不会赏鉴,满脑子净是花了多少钱,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 又复从一个小圭门里进去,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株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到廊尽头处,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将进去,便是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的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 这便是沈琼枝的院子了,“沈娘子你先休息着,我们就不打扰了。” 沈琼枝看了看院中奢靡的装潢,料想这几日吃穿用度定不会短缺的,便从包袱里拿了些碎银子打发了老妈子,“妈妈也是辛苦了,这点小钱你且先收着。” 老妈子一边退却,一边接过碎银子,笑得见牙不见眼“那就先谢谢姑娘了。”转头间那老妈子出了院子的门,就没往原路返回,反而是折了另一条道路,去回复宋为富。 宋为富坐在自己的院子里喝茶,问道:“事情可都办妥了?” 老妈子回到“办妥了,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新娘开始是淘气了些,后来倒也乖巧了许多。人嘛倒是生得标致,只是样子觉得忒赖,看起来不是个好惹的。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回头调教调教便乖顺多了,保老爷您满意!” 宋为富“我倒管不到她好不好惹,我虽为巨富之家,对妾室对要求也不高,识得了几个大字,会背几首诗就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做妾嘛,模样上得了台面就行。”又转头看向管家“你明日且到他们到下榻到店里,吩咐账房中兑出五百两银子送与沈老爷,就说‘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这里,我们会好生待着的。’收了银子,想必他也没的话说。” “这新进门的这小妾好生值钱,老爷花了五百两银子呢!”见管家与老妈子退了后,一个衣衫轻薄的女子,从床帐里走了出来,模样倒是不如沈琼枝,但身段和入骨的柔媚,沈琼枝这种良家女子是万万比不上的。 “老爷,月季也没见您掏那么多银子给我赎身呢!” “她爹可是教书的先生,她什么都不是,这几日让她先放松警惕!” “老爷,那月季呢?月季是什么呀!” “你是我手里的最艳的花。” “原来我只是一朵花啊!”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啊!”宋为富拉着月季的手,走进床帘里。 “讨厌!老爷!” 一夜过去。 “老爷!老爷!不好了!”一大早管家就慌慌忙吗敲了门! “什么事,这么急躁?不能等我出来了再说?”宋为富拿起搭在衣架上的衣服,旁边的月季服侍着他穿衣。 “那沈先生一听我这话,忙叫不好,说:‘那宋为富分明拿我女儿做妾,这还了得!’一径走到江都县喊了一状。那知县看了呈子说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么肯把女儿与人做妾?盐商豪横怎至于此!’就将将呈词收了。” 宋为富一拳砸向那黄花梨的桌子,茶杯碰出清脆的声响,旁边的女人娇滴滴捶了下男人的胸口,嗔怒着“老爷,你坏,吓到人家了!” 宋为富思索片刻边说道“我已经晓得了这事,你派一个小司客先拟一个诉呈,今晚我请知县吃顿饭,好好解释一下这个沈琼枝是个什么做派!再备点薄礼,打点一下,明日你再递交这个诉呈,他不会不给我几分薄面,我就不信这个姓沈的还有什么闹的!” 宋为富请知县在大丰旗下的酒楼里吃饭,一桌好菜好酒!知县忙道“不必如此破费!今日你请我来所谓何事?” 宋为富“愚弟今日是有一事相求!” 知县答道“这,是公事还是私事?丑话说在先,公事公办、我可绝不含糊!” 宋为富摆摆手“我明白、我明白的!你且先听我说!”先是扬言自己如何开府放粥,又在荒年捐了多少银子,又领来两个乞丐上演了一出富商慈悲心肠的好戏!演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两意绵绵,最好的名角都比不得他半分! 知县不知他要做何事,只见宋为富拿出薄礼,呈给知县“愚弟不才,扬州城里的百姓都称我一句‘贤商宋为富’,今日是想捐赠百两银子租城郊一块儿地皮施粥用。” 知县大喜“施粥是好事,不必特此上报,素闻贤商美名在外,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二人谈天说地,对沈琼枝一事只口不提。几轮酒后,知县对宋为富此人颇有几分好感,见了沈大年的折子便有了想法:都说宋为富此人宅心仁厚,怎就他沈大年递了诉呈,面上不显,便问到“你近日可是娶了门小妾?” 宋为富心里一喜,想到:不枉费我一番折磨,终于来了!“这、大人是如何知晓的?” 知县问道“只是问问,没别意思,贤弟不必在意。” 宋为富自己便张口答道“是了,本是不愿再娶了,只是那女子的父亲竟偷偷把她送上了我家门,我也无法,只好再收了一门,大人,这小妾可是有什么不干净的?” 知县笑到又喝了一口酒“没有没有,只是随口一提,喝酒吃菜。” 次日,呈子批出来,批道: “沈大年既系将女琼枝许配宋为富为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门?显系做妾可知。架词混渎,不准。” 那诉呈上批道: “已批示沈大年词内矣。” 沈大年气得哇地一口血吐了出来,整个人浑浑噩噩又补了一张呈子,说那盐商为富不仁,知县藏污纳垢。 知县眉头一皱,旋即召他们二人对簿公堂! 宋为富一口咬定是沈大年收了他五百两银子! 衙役在沈大年的包袱里搜到了几张银票,赫然正是还给宋为富的那几张银票! 沈大年直呼冤枉,定是有人栽赃嫁祸! 宋为富在一旁喝到“你这老爹!我原以为你是个知书达理的,没想到竟如此血口喷人!你说我奸狡虚伪,这扬州城总不能人人如此!大人您尽管寻证人,哪里有人动过他的包袱!” 宋为富能张口如此,显然是早已打通了大丰旗下店里所有的人员!小儿、掌柜都上堂来,作证没人动他的包袱! 沈大年一看就知晓,自己早已输得彻底!“女儿!终是爹爹害了你啊!”旁人看见一人公堂大哭大笑,这人竟是疯了! 知县见其如此,问也问不出话来,只能定案其是个刁健讼棍,一张批,遣了两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沈琼枝在这一呆就是三五日,已把这宋府逛了个彻底。 看着院子里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绿树黄树相杂糅,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各个时节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一年四季不觉得寂寞。 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盘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沈琼枝驻足在此,望向深深的墙壁,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不见消息,想道:“那宋为富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安排我,不如先逃离了了他家,再寻办法。可这宋府管教森严,只有这后门稍有松懈,只是自己身边总是跟有人,不方便逃跑。该如何是好。” “这是新来府上的姐姐?”未见其人,便闻其声,声音软媚娇俏,柔情似水。待那身影从盘虬的枝叶后走出,正是月季,月季柔柔地打了个招呼,随沈琼枝的视线看向墙,开口“这花可神奇了,虽是现在不怎么显眼,但开花的时候可不一般,满眼的珠光宝气,漂亮极了。不知姐姐,不知姐姐是否也如此?” 这女人说话夹枪带棒,来者不善“姐姐说得这是什么话,姐姐比我先来府上,那定是我称一句姐姐了!” 月季最怕别人提起她的年纪,一噎“好你个小贱蹄子,你等着!” 沈琼枝想等着就等着,我马上就要跑了,还要你收拾我?立马反驳道“姐姐可要快点啊,我就在这等着呢!” 是夜,沈琼枝躺在床上思索办法,只听见一阵悉悉簌簌,有人打开了门朝她床边靠近,听脚步虚虚浮浮,不像个习武的人。 沈琼枝心里一乐,正愁瞌睡来了没枕头,枕头这不就送来了。 “呵”沈琼枝猛地睁开眼,便把那黑影吓了一跳,月光底下一个孱弱的身影握着匕首正瑟瑟发抖,正是日夜跟着她的小婢女白梅。 “你可知道,下人谋害主人,是要被刺字发配到籍坊的?” 籍坊中女子比青楼女子更低贱,永世不得赎身,多活不过三十。 白梅桃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头嗑得咚咚作响,泪如雨下:“沈娘子,求您了,奴婢伺候您这么几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回成命吧!求您了!” 半夜里,只听得那磕头的声音,如同咚咚的擂鼓声,沈琼枝眼皮也不抬,优雅地品着茶,直到白梅额头上已然见了血,才微翘了葱白的指尖弹弹茶水,淡淡道:“规矩便是规矩,何况有错便罚?” 白梅上前保住沈琼枝的小腿“沈娘子,求求您!白梅不想被发派去籍坊,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傻姑娘,我怎么会要你去那地方,只让你帮我个小忙,事成之后,我还给你奖赏呢!”沈琼枝从自己梳妆盒里拿了枚簪子,金簪子上面镂空刻了鸳鸯戏水的样子,好不贵气。“你先收着这簪子,等办成了事,少不了你的好处!” “沈娘子!您,这、这是要白梅做什么?”小小年纪的姑娘显然没有见过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府上宠妾才有的好东西。 “很简单,你去偷一件老妈子的衣服来!别问原因,越快越好!” 白梅一回来,沈琼枝就动了,将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又从衣柜里寻了最贵的裙子,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 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清晨出了钞关门上船。那船是有家眷的,一船男女老少,沈琼枝裹得严实,也不觉得突兀。 船夫问到“妹子,我这船往北去常州,你可是要去常州?” 沈琼枝上了船,自心里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乡人家耻笑。除了家里又有什么地方可去呢?一边张口答道“是了,要去常州!” 恰逢旁边一个小孩问向自家父母“爹爹,你说那南京城真有那么好吗?我何时才能去南京啊!” 男子摸摸他的头“等你上的了府学,中了秀才再说吧!” 沈琼枝心里一动:是了,南京!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再者遇到些出路也说不定。” 立定主意,便找了船家,船家回到“你要去南京,怕是先得到仪征,换了江船才可以,我这小船可到不了。”沈琼枝连忙道谢,便到了仪征换了江船,一直往南京来。 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蒙。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象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沈琼枝住在王府塘房子里,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回来。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挂了招牌,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托刺绣的。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的来物色,非止一日。这一日烧香回来,人见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庄非熊却也顺路跟在后面,看见他走到王府塘那边去了。 庄非熊次日来到杜少卿家,说:“这沈琼枝在王府塘,有恶少们去说混话,他就要怒骂起来。此人来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听见这话,此时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我正要去问他。” 当下便留庄非熊在何房看新月。又请了两个客来:一个是退衡山,一个是武书。庄非熊见了,说些闲话,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杜少卿道:“无论他是怎样,果真能做诗文,这也就难得了。”迟衡山道:“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书道:“这个却奇。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只恐其中有甚么情由。他既然会做诗,我们便邀了他来做做看。”说着,吃了晚饭。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说,今日已迟了,明日在舍间早饭后,同去走走。”武书应诺,同迟衡山、庄非熊都别去了。 次日,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早饭后,同到王府塘来。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门首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杜少卿同武书上前一看,里边便是一个十八九岁妇人,梳着下路绺裘,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在里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听,才晓得是人来买绣香囊,地方上几个喇子想来拿囵头,却无实迹,倒被他骂了一场。两人听得明白,方才进去。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也就渐渐散了。 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连忙接着,拜了万福。坐定,彼此谈了几句闲话。武书道:“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所以来请教。”沈琼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疑猜我的心肠。我平日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这句话不错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还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内,”沈琼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谒夫人,好将心事细说。”杜少卿应诺,同武书先别了出来。武书对仕少卿说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清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入。却伯是负与斗狠,逃了出来的。等他来时,盘问盘问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说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门首,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来的正好。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你就在这里看看。”让武正字到河房里坐着,同姚奶奶进去,和娘子说了。 少刻,沈琼枝坐了轿子,到门首下了进来,杜少卿迎进内室,娘子接着,见过礼,坐下奉茶。沈琼枝坐上首,杜娘子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则坐在窗栏前。彼此寒暄,杜娘子问道:“沈姑娘,看你如此年轻,怎么独自一个人在外边,可有个同伴?家里可还有尊人在堂?可曾许过人家?”沈琼枝道:“家父历年在外坐馆,先母已经去世。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线活计,来到这南京城里,寻个去处,借此糊口。适承杜先生相顾,相约到府,又承夫人一见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针线活儿做得是真的好。昨日我在对门葛来官家,看见他相公娘买了一幅绣的‘观音送子’,说是买的姑娘的,真的画儿也没有那绣的画画得好!” 沈琼枝连忙摆手:“胡乱做做罢了,哪值得您这么夸赞了。” 几盏茶的功夫,姚奶奶边说“在这都吃了好几碗茶了,我也该回去了!”随即走出房门。 沈琼枝见姚奶奶出了外门,便在杜娘子面前双膝跪下。 杜娘子大惊“你这是做什么!”连忙扶了起来。 沈琼枝便把自己心系萧采,盐商骗他做妾,她拐了东西逃走的话,说了一遍,“而今只怕他咽不下这口气,还要追踪而来。夫人能不能救我?” 杜少卿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竟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但他必要追踪,你这祸事不远。却也无甚大害。” 正说着,小厮进来请少卿:“武爷有话要说。” 杜少卿走到河房里,只见两个人垂着手,站在窗子门口,像是两个差人。少卿吓了一跳,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怎么来我家?” 武书接应道:“是我叫进来的。”拿出一张拘捕令,递给杜少卿“奇怪!如今县里据着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说他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妾。”努努嘴朝内室“那个、我看得没错吧?” 杜少卿看也不看把拘捕令对折还了回去道:“是了,如今她就在我家。”看向两个官差“你们在我家抓走了人。就像是我家指使你们来抓;传到扬州去,又像我家藏留她。她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只是这个倒有些不妥帖。” 武书道:“小弟先叫差人进来,正为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赏差人些微银子,叫他仍旧到王府塘去,等她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她,不就好说了。”杜少卿依着武书,赏了差人四钱银子。差人得了好处也就依着去了。 少卿复身进去,姚奶奶看见官差在河房,也一道留下了。 杜少卿将这一番话向沈琼枝说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沈琼枝明白其中道理,自己这是已经连累到了,起身道:“这个简单,差人在哪里?我同他一路回去就是了。” 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回去了手帕巷了,你且用了便饭。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 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自己走到河房里检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等着武书写完了诗,又称了四两银子,封做程仪,叫小厮交与娘子,送与沈琼枝收了。随即又喊了小厮寻来一顶轿子,抬着沈琼枝出了门。 沈琼枝告辞出门,上了桥,一直回到手帕巷。那两个差人已在门口,拦住说道:“还是原轿子抬了走,还是下来同我们走?进去是不必的了。” 沈琼枝道:“你们是都堂衙门的?是巡按衙门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钦案的官司,哪里有拦着我不让我回家到道理!你们这般大惊小怪,是把我当作那大字不识的乡里人吧!”说着,下了轿,慢慢地走了进去。两个差人倒有些杵她。 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出来叫:“轿夫,你抬我到县里去。” 轿夫正要添钱,差人忙说道:“千差万差,来人不差!我们一大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给足了你们脸面,又在这等你轿子回来。就连你哥女人都要吃饭喝水,我们几个难道是茶也不吃的?” 沈琼枝见差人想钱,全当没听到,只给轿夫添了二十四个铜板当作轿钱,让他一直就抬到县里来。 差人想要银子,又没有正当理由了,无可奈何只能一路抬回县衙里去。走到县衙门口回禀道:“缉拿的那个沈氏到了。” 知县听说,便叫带到三堂回话。带了进来,知县看她容貌不差,问道:“既是女流,为甚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本县地方做甚么?” 沈琼枝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涉了讼,他买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 知县道“你骗了那么多人,我怎知你此话是真是假?” 沈琼枝道“我若骗人,只骗坏人,知县清正廉明我自不会说谎” 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原可以求教的。”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 这诗做的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随叫两个原差到他下处取了行李来,当堂查点。翻到他头面盒子里,一包碎散银子,一个封袋上写着“程仪”,一本书,一个诗卷。知县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关文,吩咐原差道:“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一路须要小心,不许多事,领了回批来缴。”那知县与江都县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 这时日庄征君来信了“前几天我听闻了常州女子的事情,她的确是亮丽洒脱,世间少有。平庸之辈会感到惊疑,而开明之士则会为之兴奋。但是,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有目的性,都是先有目的才开始最初的行动。然而,这位女士虽然卓异不凡,我却看不出她的目的何在。 火得薪而能明,月近日而有光,阴必附阳,柔必倚刚。天地生物,各有其方,违其道而能济者,未之前闻也。她既然出身名门,又嫁于巨室,岂可一举抛弃两个家庭,难道两家的亲属就没有一个好人吗?这难免令人生疑。作为一个飘零之孤女,却屡设机关,谋人之利,况且又没有正当理由。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资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难道她想学红拂女投奔李靖?或者学卓文君追随司马相如?可是现在早就没有李靖、司马相如这样的人了啊。 你有崇尚奇异之心,又有行仁仗义之志,并且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你何不引导这位女士走上正确的道路?令其幡然改悔,回到家中,与父母等亲族商量,选择有德之士改而嫁之。你能做成这件事,对这位女士则是功德无量,对你自己也是行善积德。” 杜娘子答道“是啊,我也觉得那样一个奇女子沦落至此,我们却没有帮助。”她想了想“她那日提到那负心汉可是萧采?” “她那日是那么说的,那萧采竟和那萧云仙同名,真是巧妙,可二人净是云泥之别。” “我看不竟然,她小时候在青枫城待过一段日子,那萧云仙也在,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你是说,这二者是一人?” “恐怕其中必有蹊跷,这萧云仙如今还在南京城,夫君,你且快去寻他。”杜娘子忙催到。 “我这就去!”杜少卿赶忙披衣,叫小厮牵了马来,过了朱龙侨,到了广武卫地方,急急朝那萧云仙下榻的驿站去,甫一进门便高声喊道“萧云仙可在?” 那萧云仙从窗檐中探出半个脑袋“原来是杜少卿!今日来访,可有何事?” 杜少卿急急下了马,小跑着上去“此事事关紧急,我就长话短说了!你可认得那常州的沈琼枝?” 萧云仙脸色一遍,急忙问道“琼枝?她出什么事了?” “盐商骗她做小妾,她偷了人家东西跑了,现在被捉回江都县衙门了,你若快些赶回去,还来得及!” “少卿,借你马一用!”那萧云仙披上外袍,就骑马去了。 当下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雇轿子抬到汉西门外,上了仪征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头上,锁伏板下安歇。沈琼枝搭在中舱,正坐下,凉篷小船上又荡了两个掌客来搭船,一同进到官舱。沈琼枝看那两个妇人时,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一个十七八岁,乔素打扮,做张做致的。跟着一个汉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顶破毡帽坎齐眉毛,挑过一担行李来,也送到中舱里,两妇人同沈琼枝一块儿坐下,问道:“姑娘是到那里去的?”沈琼枝道:“我是扬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妇人道:“我们不到扬州,仪征就上岸了。”过了一会,船家来称船钱。两个差人啐了一口,拿出批来道:“你看!这是甚么东西?我们办公事的人,不问你要贴钱就够了,还来问我们要钱!”船家不敢言语,向别人称完了,开船到了燕子矶。 一夜西南风,清早到了黄泥滩。差人问沈琼枝要钱,沈琼枝道:“我昨日听得明白,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 差人道:“沈姑娘,做人也不能这么不厚道!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沈琼枝听了说道:“我便不给你钱,你敢怎么样!”说罢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提朴刀的差人方一走近,就被沈琼枝喝到一声下去!一飞脚踢中腰部,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另一个差人忙抽出刀急着转身,沈琼枝右脚早起,扑通地也将他踢下水里去。“你们竟想对你姑奶奶下手!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三脚猫对功夫!” “你这泼妇” “你这泼皮差人。” 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汉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轿子,两个差人跟着去了。 江都县,县衙。 白知县坐在上堂,见到被轿子抬上来的沈琼枝,白知县看了看手上的信“听闻你素有才气,吟两句诗来听听。” “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 “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 白知县拊掌叫好“好好好,确实有几分才情。你且说说你为何不愿嫁。” 沈琼枝就把那富商如何骗她,府中如何奢靡,白日歌舞不断描绘了一遍。 白知县心中也有了计较,道笑问道:“那你还愿不愿意跟了那宋为富?” 沈琼枝答道:“本是要娶我为正妻,但三书六礼一个都没有,只空头就想娶我?” 白知县笑到“那这三书六礼都补上了,你可还愿嫁给他?” 沈琼枝笑了“不想。” “你这小娃娃,竟不知好歹,正妻也不做?” 沈琼枝道“怎可以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 白知县道“你这小姑娘,那你说你想嫁谁?难不成谁也不想嫁不成?那我可判不了,你既没有心上人肯娶你,也不愿为小妾,你这名声传出去可不得了。” 沈琼枝正着急上火,只见后面快马进院,一众衙役都拦不住“我娶!” “萧云仙,你怎么来了?还擅闯公堂。”白知县。 “事出突然,还请知县不要怪罪。” 沈琼枝听见熟悉的声音,连忙转头去看,果不其然,萧采就是萧云仙“你个负心汉,大骗子,我嫁你做什么?” “琼枝,你听我解释。我姓萧名采,字云仙。从头到尾我没有骗过你。我本想回青枫城按约定娶你,可突然派了我押解货物去京城,军命难违,我只得写信回去,可谁知阴差阳错,你恰好离开,我与你父亲相见,本想就此提亲,谁知竟得到了你订婚的消息,一时间我失魂落魄,也难辨此事真假,再回来就是几个月后了,还好杜少卿告知了我真相,不然我真的被瞒在鼓里。” “这、我竟不知......” “这还要说什么知不知的?你的名声保住了,还寻的了有情郎。”白知县一听,乐了“郎情妾意,好嘛好嘛,有情人终成眷属,可喜可贺。那这批文我就批你们二人择吉成婚!哈哈!” 皆大欢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fb/15901.html
- 上一篇文章: 国家发布了全国重点镇名单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