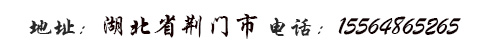大地上的母亲
|
北京哪里白癜风医院好 http://m.39.net/pf/bdfyy/bjzkbdfyy/大地上的母亲文/王新程-01-母亲庚子年腊月初六往生。我们为她超度后,把她安顿在屋后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塞。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七七”。在我们老家,人离世后,只有过了“七七”,才算真正断了尘世之念,安心前往乐土。所以七七也算得上是告别的大日子,到那天,亲戚们都会赶来“烧七”。头天下午,我就从北京赶回老家。七七那天早晨,我们一家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虽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今年春天来得早,人间春风浩荡,母亲的坟还是新土,但墓碑的缝隙间已经冒出细嫩的青草。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她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我始终觉得,我的母亲是属于大地的。她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和她供弟弟读书。差不多一长成,她就开始劳作,跟家人一起从地里刨食,把自己养大。成年后,她嫁给一个同样贫穷的农人。在大地上,她诞下四个儿女,最后存活三个。她跟丈夫在地里种红苕、洋芋、苞谷、大豆,把三个儿女养大。年轻时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是方圆几十公里出名的美人。但土地消耗了她,磨损了她。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多岁,但仿佛已经在人世忍耐了好几十年。她在土地上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颇有点聪明的丈夫,生养了一群让人欣慰的儿女,其他没有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裳,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看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土地。土地养育了她和她的儿女,也耗尽了她的一生。85岁上,大地召了她回去。她躺进她生前一直耕种的一小片土地里。她来这世上一遭,像是一个必然,又像是一个真理。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泥土色的真理。一个像大地一样开阔、沉默、深厚的真理。年,我从丹江口调国家环保总局工作,父母到北京来看我们。-02-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集体,母亲每天早晨下地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人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去就吃奶。等我吃完,母亲才出门。近晌午,我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等母亲抽空过来喂奶。那时候大集体劳动人多势众,地头点苞谷像打仗,社员排成几个个纵队,刨垄、打窝、点种、盖肥、瓮土,流水线作业,齐头并进,争先抢后。队长背着手,在壕垄间查质量、催进度。母亲一到了晌午就开始东张西望,一看到我的小脑袋从桐花中探出来,就跟队长撒谎说解手,扔了锄头就朝我跑来。我噌噌噌从树上溜下来,撩开母亲的衣襟就开始吃奶。有天我吃得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原来母亲离开久了,她那条流水线的社员都闲坐在地头。队长很生气,就寻过来,喝斥我的母亲。队长真凶,训得母亲直淌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当晚回家,母亲就用锅烟灰拌了煤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我躺在床上,不敢出声,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煤油灯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地淌泪,觉得被母亲抛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那是我跟母亲的第一次离别。年,父亲出院后,父母回到哥哥家。那天嫂子不让母亲帮忙,大家请她坐在桌前等开饭。她仿佛有些不习惯。-03-多年以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前面说过,我的母亲生了三男一女,最后成活了我们姐弟三个。起先,在我的头上,是另外还有一位哥哥的。只是那位哥哥在半岁时得了病,没养得过来。母亲从此得了心口疼的病,经常没来由地心疼和惊慌。我出生后,她像是得到了补偿,但同时又怕把我弄丢了,半夜里常常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我两岁时有次得了病,发烧几天,几乎不保。那时候父亲作为生产队里的匠人,常年在外走村串乡做一些手艺活,给队里挣钱。母亲带着祖母和三个儿女在家。我病得很重,母亲着急伤心得六神无主,祖母喝道:“还不快去请医生!”母亲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跑去邻村请医生,一边跑一边哭。那位乡村医生行医之余,竟学做了道士。遇到病人,一般先治;治不好,转身就换上道士的衣服,做道场替亡灵超度。我母亲去请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人家做道场。母亲顿觉这是不祥预兆,哭得说不出话来。那位身着道袍的医生问她是来请医生还是请先生。我们那里,把道士、占卜的、算命的、看阴宅的都称“先生”。母亲哭着说儿子病了,请医生。那位医生兼道士说把眼下这场道场唱完才有空。母亲急得又大哭起来,求医生赶紧救儿子的命。医生让她报上我的生辰,说先测测八字。一测,问了是个男孩,连说“不怕,不怕”,让母亲先回家,他唱完道场就过去给我瞧病。母亲只得一边哭一边回家。当天晚上,那位医生真的赶来了,他给我烧了灯草,灌了汤药,烧就退了。接下来几天,吃了几副药,我就痊愈了。病愈后我一直很虚弱,母亲就又让我吃起了奶。这样就一直吃到五岁才断奶。母亲很坚决,可能也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孩子走不远”的话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了七八里外的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一起听课。这样,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我就正式成了一年级的学生。我的老家叫官渡滩,寨前有条河,叫董河。河水清浅,游鱼如织。村人常用自制土炸药炸鱼。一只雷管点着了,朝河中央扔,轰的一声,鱼就一阵阵翻了上来,白哗哗的浮在水面上。炸鱼是很危险的事情,雷管扔早了,掉到水里,把鱼吓跑了;扔晚了,在手里就爆炸了,把人炸出个窟窿,或者炸掉半只手是常有的事。母亲严禁我炸鱼。凡是所有危险的事情她都坚决禁止。但男孩子哪里禁得住诱惑?有一次,我跟着寨里的孩子去河里炸鱼。雷管刚炸响,就听到一声惨叫,扔雷管那个人的手炸没了,剩下胳膊茫然举着,像棵断树桩不断涌血。我们都吓懵了,随即大哭大叫起来。母亲听到爆炸声,又听到哭声找到河边,看见受伤的那孩子,呆住了。等大人们手忙脚乱把受伤的孩子抱走,她才醒悟过来,抱住我就哭,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掐着我的胳膊,像要掐在手里才放心。等到河滩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搂着我,抽噎着回到家。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第二天,医院里,无甚大恙,但残疾肯定的了。她仿佛这才醒悟过来,揪住我就打。她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她说人有三怕,怕天地,怕活物,怕鬼神。“你不怕我就打,打得让你怕。”她打完,又抱着我哭。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烁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当年打骂我时说到的怕。我想,母亲说的“怕”,其实应该是敬畏吧。敬畏星空,敬畏自然,敬畏法则,敬畏道德,敬畏生命,这是一个人苟活于世而不乱的底线。我家门前的河-董河-04-一生都向土地俯首,把力气和心血都给了土地,土地却并未回报她。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一个男子十分工分,妇女只有七分,跟老人和半大小孩一样。每年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姑姑到我们家,走两个小时山路。家里的晚饭是苞谷面稀饭掺四季豆叶。父亲用筷子搅了搅,稀饭里都是四季豆叶子,看不到多少苞谷面,就把碗往桌上一顿,脸就黑了下来。他说妹妹大老远的来,不应该放这么多四季豆叶,应该多放点苞谷面。可是哪有多的包谷面呢?其实姑姑一进门,母亲就拿着碗准备找邻居借一碗米。但她临出门时拿着碗立地在门边,自言自语:“晓得别个有没得”,“借了又哪个时候还别个哦”,犹豫了好一会,最终还是没有去借。父亲那晚的怒火很久不能停,母亲在灶前垂着头抹泪,姑姑劝了父亲,又劝母亲,最后也哭了。每到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山里有枇杷,村人就剥枇杷树的皮,连夜用锅炒干,用石碓舂成粉,混点草叶捏成面团蒸熟了吃。没过几天,山里的枇杷树皮都剥光了,枇杷树一棵棵枯死。母亲想杮子跟枇杷一样都是好果子,杮树皮该也能吃吧。于是剥了杮子树皮,也和了草叶做成面团子。头一个先端给饥饿的老祖母,祖母吃了一口,被噎得差点死过去。母亲吓得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给我的面团子也掉地上了。我虽然又饿了一顿,但总算躲过一劫。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地角种了南瓜、黄瓜、玉米。黄瓜刚打出指头样的胆儿(我们那里把作物果实初长叫打胆儿),南瓜才开花,玉米的腰上刚冒出一缕细嫩的红樱,就被大队干部巡查到,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大队干部连铲带拔,骂骂咧咧,十分凶狠。我捡起石块就要砸干部,母亲抢下了石头。我冲上去就要咬干部,母亲抱住了我。她说扯掉几根庄稼是小事,伤了人就伤天理了。不让人活命算不算伤天理呢?我不明白,但我从此心里就开始恨那些坏官。家家都养猪。人都养不活,猪就更难了。而有的家庭,干脆就养不起猪了。我每天跟姐姐打猪草,把猪草剁碎后用大锅煮熟,早晚各喂一顿。每户杀了猪,剖成两半边,一半边必须卖给食品站,留半边自家吃。剩给自家的半边,差不多只有五、六十斤。除了杀猪当天及春节有点猪肉吃以外,平时都没吃过肉。但菜里总得有点油星子。母亲把猪肉切成舌头样的长片,炒菜前将肉片放在锅里煎一下,眼见锅底有点油出来,赶紧把肉片提起来,把油滴尽,又挂起来,下次继续使用。薄薄的一小片肉一般用20天。我们正长身体,馋得很,看着母亲把肉片放在锅底煎油,就盼肉片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多浸出两滴油。每次母亲几乎是坚定地把肉片从锅底捞起,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把越来越瘦的肉片挂在碗柜旁边的铁钉上,嘴里就涌出许多清口水。年10月4日,父母、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在重庆参加侄子王翼婚礼,左一为姑姑、左二为舅妈、右一为姑父、右二为舅舅、右三为父亲-05-艰辛的日子也有意外的惊喜。遇上农忙,则会有饭团子吃。那美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大集体劳动,三月点包谷,五月插秧,六月收麦,九月割稻,抢种抢收,那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每到这些农忙的时候,生产队会集中做午饭派人送到地头给社员吃,这样就省了社员回家吃饭的时间。每天天黑,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放下农具,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就着油灯,小心翼翼地把手巾打开,里面是一个紧实的饭团子。每每这时候,母亲脸上的神色就是神秘的,也是得意,像从人世里偷到了一个宝贝。她把饭团子掰三块,我们姐弟仨一人一块。那时候生产队也是举全队之力,饭团真是香,苞谷面里还掺着白米,那是要等到过年或家里有客人时才能吃到的。我们拿在手里就迫不及待地吞下去了。有一次,饭团里还破天荒地夹着些肉丁酸菜末,使整个饭团都浸着肉香。就是那点肉香,让我们姐弟仨舔了半天手指头。那时候我们都盼着农忙。农忙是我们额外的节日。多年以后,我在跟一位婶娘的聊天中,才得知,农忙时节每个社员在地头吃到的大锅饭是限量的。母亲是忍了饥,吃了半碗,就把剩下的饭捏成团带回家。怪不得她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农活太重,又吃不饱,她回家时完全是接近忍耐的极限了。遇上赶集,母亲回到家,会从衣袋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粒水果糖——只一粒——就是那种七八十年代,乡村供销社里常卖的那种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硬糖,琥珀色的——偷偷递到我的手心,像地下党员交接情报,并给我使眼色不能让姐姐和哥哥知道。我把糖紧紧攥在手里,像握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跑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剥开糖纸,把糖粒放进嘴里,久久地噙着,舌头时轻时重,生怕吮轻了,甜味就跑了;又怕吮重了,糖一下子吮没了,糖纸也不舍得扔,蔵起来用舌头舔,也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我一次又一次秘密地吃下她买来的糖果,有一次,忽然良心发现,把糖让给她也尝尝。结果她答:“尝过了。”我惊问她怎么尝的?她不好意思地说:“赶场回家的路上,悄悄剥开糖,舔了几下糖纸。” 年三月初一,母亲83岁生日,儿孙们为她祝寿,我们姐弟仨向父母敬酒 -06-一辈子耕种、生养、劳碌、忍耐,低眉颌首孝敬婆婆,谦卑柔顺侍奉丈夫,呕心沥血养育儿女,温良慈和对待亲邻。官渡滩的六十多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从没对人红过脸,连妯娌和姑嫂之间,也处得像亲姐妹。她常说人一世不好过,要学会低头。哪里只是学会低头呢?她一辈子都在低头中度过。一生中跟父亲吵过两次架,都是因为我。那是我十岁那年,大年三十,我没上山放牛,想用干草和麦秸敷衍一顿。父亲不同意,我就顶嘴,他就打我。我性子特别倔,任他劈头盖脸地打,一声不吭。父亲更气,让我跪下,我不跪,他操起扁担又打我,我就往后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去处,就往姑姑家走。走了两个小时,沿途见人家都在放鞭炮过年,而我却被赶出家门。我边走边哭,走到姑姑家时,眼睛都哭肿了。初一早晨,姑姑送我回家,见母亲坐在门口抹泪,一见我们,就赶紧迎上来。父亲站在院坝里,悻悻的想过来搭话,我横了他一眼,不理他。父亲把我赶走后,母亲非常生气,跟父亲大吵,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都没做。她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整夜都在哭泣。母亲看到我,哭着说:“一个人不认输,不低头,这一辈子怎么走下去呢?”谁说我一辈子不低头呢?多年以后,她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把她放平,长久地跪伏在她床前,额头贴地,想倾听大地传来她离去的足音。她的儿子曾经那么骄傲,以为只要努力,就无所不能。但命运挫败了他,夺走了他的母亲。这个失败的儿子,在母亲临终时刻,终于向命运低下了头颅。年9月14日,父亲在官渡滩老家高血压发作后摔倒,我们立即接到重庆,医院三院,受到我兄长般的朋友李华副院长悉心治疗和亲切关照。那段时间母亲寸步不离,在医院照顾父亲-07-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奶,得母亲的恩情比常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病痊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背水、打猪草,也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上学下学每天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第一。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也不咳嗽不打喷嚏。有时候惹恼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打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所有农家的儿子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我本来可以跟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也许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或者深圳,去工地下苦力,搭钢架、制模,或者进厂里旋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在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马路边起个楼房。但我念书实在机灵。老师教的课也有趣。我很害怕自己像村里的男人那样在土地上把一生耗尽。虽然我未曾像一个正劳力一样在土地上劳动,但心里已经对这种生活十分厌倦。我只有认真念书,才能躲在教室的屋瓦下,避免日晒雨淋的命运。我门门功课都满分,父亲觉得念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这还是个正途。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非常敬重念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也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缝鞋子于我的母亲,真是一件好事情,她陪着母亲消磨了多少时光啊。她埋头仔细地抽针纳线,这事单调枯燥,无休无止。我有时候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正看着我,母子俩眼神在交汇间,仿佛得到了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埋头学习。有时候母亲傍晚才从地里收工回来。天黑尽了,她点着油灯做饭。我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灶前,就着跳跃的火光写作业。一边写一边往灶膛里添加柴禾。母亲在灶后忙碌不一会,锅里的香气就升起来了。我忍不住咽口水,母亲用锅铲铲上油渣给我,我拈起放进嘴里,又香又烫,就解了馋,赶紧又低下头去,就着火光继续写作业。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时因为忙碌而顾不上的活,裁豆子,剥苞谷,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那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明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有时候,我悄悄抬头看母亲,看她正入神地绱鞋底,或者绗鞋面——鞋尖的关键处,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外面风雨琳琅,无休无止。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嘀嘀嗒嗒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因为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而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就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的节日。我十岁时从黎家村小毕业,考入区重点中学一一双河中学,初一时在学校留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08-我们姐弟仨同时上学,开学时经常凑不够书学费和生活费,只得四处去借。父亲会一些乡间的手艺,譬如修轧面机、补油桶子。农闲的日子,就走村串户挣点手艺钱,交给队里,余下的就留下来,偿还欠下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母亲还钱总是很准时。她总告诉我们,有难时人家帮一把,要记情;以后长出息了,一定要还别人的情。村小在离家七、八里外的地方。我放学时遇雨,穿着布鞋趟水回家。母亲非常愤怒,抓过竹鞭就朝我抽打,我满脚泥水,被打得双脚跳。姐姐大呼“弟娃儿快跑”,我偏不跑,仰着脖子让她打,一声也不吭。想到她夜里千针万线缝出来的鞋,被雨水一泡,就层层烂掉,我也很后悔,一边挨打一边流泪。那是我上学后母亲唯一一次打我。自那以后,无论天晴落雨,我上下学都打赤脚。一出门就把鞋脱了放到书包里,撒开腿就跑。跑到学校门口,再穿上鞋。姐姐心疼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人的脚就得沾地,沾泥土,泡雨水,大地补人啊。多年后我为人父,对着星子一样的女儿,含在口里都怕化了,遂想起童年沾满泥水的双脚被她打得乱跳,想到从此后我赤脚在那条路上跑了五年,风雨无阻,想到她说赤脚走在大地上是大补,就有些疑惑:我或许是真得了大地的补养恩赐,年过半百,我从没穿过秋裤、棉靴。大冬天里,当人们穿戴得严严实实,像熊出没,而我干练抖擞,从不畏严寒、怕疲劳。这是你给我的恩惠,母亲。有一日,父母来京,周末的午后,我忽然轻狂,拿出我的一些证书给父母亲看。母亲看那些大大小小、印制精美的各色本本,就很喜欢。她拿在手里反复摩挲,粗糙的手擦挂得证书的缎面扑哧扑哧地响。我告诉她每个本代表什么,她就又茫然了。父亲认得那些高级职称、领军人才、博士博士后的字样,同时也知道那几个大学都是很有名的,于是又很得意。我笑说这点出息都是二老打出来的。母亲似乎这才记起她也打过我。她似乎有些糊涂,喃喃地:“啷么会呢,我啷么就打你了呢?”她一边说,一边摊开手看,仿佛不相信她的手曾经握起过竹鞭子,抽打过她的儿子,一时间好像非常惭愧的样子。年10月4日,侄子王翼结婚,父母从老家来重庆参加婚礼。长孙王一、次孙王翼均已成家,父亲高兴得开怀大笑,母亲也开心,但却温和平静得多。 -09-母亲还有一次跟父亲吵架,是因为我年少时的亲事。土地下户后,一家人总算能吃饱了。人一吃饱,就有了不一样的理想,甚至有些好高骛远,具体就是,十五岁那年,家里为我说了一门亲事。我们那地方,一直以来时兴娃娃亲。村里好多孩子十五六岁就订了亲,两家走亲戚,要走到男女双方到了婚龄,扯了证并行嫁娶之礼。也有的订了亲,等不到婚龄,也通过郑重的嫁娶成了家,生儿育女。证不证的,就不管那么多了。我的对象是个害羞的小姑娘,比我还小半岁,长得很漂亮。她的父亲在乡里工作,是很好的家庭。就亲事论,这在全乡也数一数二,我们家算是高攀了。下了聘礼,就算结成了亲家。那年春节,我这个未婚小女婿,由父亲带着,去小对象家拜年。我的父亲很满意我们跟这个富裕家庭结亲,他指望我的岳父日后能提携我,顺带帮补帮补我们这个家庭。一家人就这么怀着希望,把这亲事走下去。但拜年时出了一点状况,毁了父亲给我设定的好前程。正月初二,我穿上新衣服,背着背篓,由父亲领着去拜年。背篓里装着拜年礼物,系着红纸的猪腿,糍粑,粉条,酒,还有给小未婚妻的新衣服。说是给未婚妻的衣服,其实也就是稍大码的童装,我记得是件桃红色的小外套,衣领滚着连,胸前绣着好看的花。一切都正常,甚至是喜气洋洋。却被我上个厕所就把事情搞砸了。那天吃过晚饭,我上厕所,踩虚了脚,掉进了粪坑。我在坑里喊“救命”,父亲和我的岳父听到喊声跑出来,见我正在粪池子里扑腾,惊呆了。他俩把我捞上来,父亲带我到河坝冲洗,一边冲洗一边骂我丢人丢到家了。我穿上岳父借给我的衣服走回他家,站在院坝里,不肯进门,我浑身发抖,身上还有一股臭味。我觉得糟透了。天快黑了,院子边的菜地里,白菜顶着白雪,立在暮色里,说不出的寒冷和孤寂。暮色从天而降,像要把黑而老旧的寨子吞没。寨子周围全是黑乎乎的大山,你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世界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黑乎乎的寨子。这时,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未婚妻正掀起窗口的塑料薄膜悄悄打量我。我又羞又恼,无地自容,真想转身逃跑。因为这个意外,当晚父亲决定带我回家。一出家门,我就跟父亲说我要毁婚。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本来就气,一听又骂。夜里我躺在床上哀哀哭泣,像五岁那年断奶时那样哀伤。母亲半夜里起来,听到我的哭声,她也流了泪。母子俩就那样相对而泣。忽然母亲大怒,这怒火不是朝我,而是对父亲。母亲暴躁地跟我父亲大吵。她一边哭一边骂我的父亲,骂他狠心,把儿子往粪坑里逼。这一骂,把父亲也骂得软了心。天亮后,父亲涎着脸去了媒人家,请媒人去女方家商量退婚。几天后,媒人带来了岳家退回的礼物:小未婚妻的新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片片;腊猪肘里被戳了许多洞,洞里灌了煤油。这退回的礼物让我的母亲很久闷闷不乐,父亲更是好些天都不理我。我母亲从不负人,但她在儿子的事情上,是终于负人了。在乡间,一家姑娘订了婚,又被退婚,是丢家族面子的事情。母亲对此一直怀着愧疚。然而人家家底旺,姑娘又实在漂亮,不久就有好人家去提亲,那户人家比我家强,儿子也比我长得俊,对方挣回了面子,气也消了。父亲始终不敢跟那家人打照面,而母亲见到,也是谦卑而羞愧。倒是那位姑娘,因为有了更好的着落,又知道我后来出去工作,跟她注定凑不到一块儿,很是深明大义,觉得当初毁了婚约,应该如此,是命定的。多年后,我回乡时遇到一场亲戚家的喜酒,在喜宴上看见了当年的小对象。当年那个漂亮羞涩的小姑娘已经年至半百,成为一个健壮爽朗、大方得体的农妇了。岁月的劲可真大啊!那一刻我真有点百感交集。她犹疑了一下,随即不卑不亢地向我打招呼。我想起当年的窘相,克制住羞愧,也向她问候。我俩掏出手机互留了电话,加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cs/16386.html
- 上一篇文章: 宋绪元诗体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