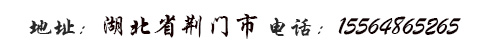疯子马爱娥
|
治疗白癜风的费用 http://pf.39.net/bdfyy/bdfal/偏戴帽,倒靸鞋,你媳妇儿叫个张有来!七八个七八岁的孩子,有男孩有女孩,穿得花花绿绿,手拉着手围成个圆圈儿,转着圈玩,一边转圈一边唱:“偏戴帽,倒靸鞋,你媳妇儿叫个张有来!”被围在圆心的是一个稍大点的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儿,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衣,蓝布裤子,千层底布鞋。她双手捂在眼睛上,羞红了脸。孩子们还在转着圈唱。女孩儿撒开手,猛地往前一冲,小圈子被冲开了一个缺口。女孩朝站在路边树下的一个男孩冲过去,气急败坏骂他:“刘永永,你这个坏种!”男孩子见把戏被戳穿,撒丫子跑了。她追着打他,也跑远了。刚刚还笑声不断的场子,忽然冷清了。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转向女孩子逃走的方向——她已经跑得看不见影子了。回头时,圈子里却多了一个人。她笑嘻嘻地说:“她走了,我给你们当媳妇,好不好?”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手背上的垢痂一层摞一层。披头散发,脏兮兮,臭哄哄,不知道有多久没洗过澡了。“马爱娥!”其中一个孩子惊叫起来,掉头就跑,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他一哄而散。马爱娥一只手正从后领伸到背上挠痒痒,摸出一只米粒大的虱子,放在两个大拇指甲中间,“嘭”地一声,血溅了一脸。她用手抹了一把,说:“你们的新媳妇跑了,我给你们当媳妇不行吗?跑啥哩?我又不吃人!”马爱娥就是这样,往往在最不该出现的场合露脸。马爱娥是齐家楼人,生年不详。那几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村里家家户户都在除“四害”,有好事者把马爱娥提升到与西晋周处相同的地位。周处与“山上猛虎、水中蛟龙”并列本地三大“害虫”,好事者也给我们乡罗列了“四害”——马爱娥,奔奔车;瓜宝升,疯天社。奔奔车就是带车厢的三轮摩托车,是远近各乡村往来市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奔奔车稳定性差,转弯时容易侧翻。尤其到了冬季,路面结冰,踩刹车如果力度不当,很容易翻车。所以,奔奔车长期稳居杀手排行榜第一位。奔奔车虽然给人们制造了灾难,却实实在在解决了农村人出行难的问题。“瓜”是傻的意思,瓜宝升是个智障,疯天社则是精神失常。他们两个和马爱娥一样,欺侮娃娃打老汉,惹得民间怨声四起。马爱娥之所以“雄居”“四害”之首,就在于其他“三害”是不得已,而马爱娥据说有儿有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偏把自己作践成了叫花子。我第一次见马爱娥,也是在这种场合。那天下午吃过饭,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瓦窑坡砖瓦厂的大平地上玩弹珠,我们用石子在地上画一个“里”字多一横的图案,把弹珠放在下面,第一次弹到上一横的位置,弹珠停止的位置要恰到好处,过线越界算输,弹不到指定位置也不能算赢。“一弹弹,二蹦蹦,三敲锣,四进城……”第四下,弹珠恰好滚到“田”字头的中心。我们几个孩子围成一圈,大呼小叫,不亦乐乎。轮到我了。我拿出弹珠,放好,又爬下去,脸贴在地地瞄了瞄,中指和大拇指箍成一个圆圈,正准备出手,忽然伸过来一只脏兮兮的手,中指在弹珠上轻轻地一弹……弹珠慢悠悠地向前滚去,越滚越慢,不偏不倚,正好停在“里”字的短横处。“好耶!”那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们这才发现圈子里多了一个人,她蓬着头,衣服破破烂烂,身上有一股刺鼻的馊味。“马爱娥……”有一个孩子尖叫起来。旁边的几个孩子都像被蜜蜂蜇到了,呼啦一下散开了,跑得远远的。马爱娥嘿嘿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黄牙。“我又不吃人,”她说,“你们把我加上,咱们一起玩嘛。”“马疯子!打她!”一个孩子拣起一个土块,朝马爱娥扔了过去。马爱娥伸起胳膊一挡,土块正好砸在她的小臂上,“嘭”地散了,土埲了她一嘴,她“呸呸”吐了两口唾沫,用手背擦了擦舌头上的土,“狗日的!”她骂了一句,跳起来去追那个小孩。那小孩往前跑了几步,又顺手拣起一个土块,回头一丢,正好砸在她的脑门上。另外几个孩子也都拣土块往她身上丢,马爱娥边躲边往后退。孩子们步步为营,马爱娥只有抱头鼠窜的份了。天黑了,孩子们都散了,我也该回家了。眼前的路笔直地通向我的家,得走上二十分钟。我慢慢往回走。路的左边是农田,右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我行走在沟壑边上,沟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夏夜的风凉嗖嗖的,地田的庄稼轻轻地摆动,沙沙作响。天上没有月亮,星星也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只有眼前的路微微泛白。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乡村的夜晚格外宁静,静得只能听见我自己的脚步。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有点零乱了,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在走这条宁静的路。我心里感觉有点怪怪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噎住了。我停下,用手在喉咙上揉了揉。脚步声好像有回音,也慢慢停下来了。我的头皮凉森森的,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加快了脚步,但脚步还是那样零乱,好像有人在和我并排行走。我又停下了。身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真有一个人跟在我的身后,她离我越来越近,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听见她说:“娃儿,你别怕,我不打人。我是看你们玩的热闹,想跟你们玩。你不知道,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心慌的很。”“马疯子!”我尖叫了一声,扯着哭腔赶紧往家跑。回到家,进了大门,我把门闩闩上,背靠着门,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惊魂未定,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鼓点一样急促而有力。家里的大白狗小白向我扑过来,两只前爪搭我的胸脯上,吐出长长的舌头,从上到下舔我的脸,舔的我脸上全是哈喇子,拖得老长,弄得我的脸黏乎乎的。我不耐烦地把它赶到一边,它又摇着尾巴跟过来,始终不离左右。父亲在外面打工,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马马虎虎啃点馒头,再背上三四个干冷馒头,就骑自行车上工地。中午在工地上对付着吃一点。晚上下工后再骑自行车回来吃饭。他有时候会加班,到家已经很晚了。我进家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哭了起来。母亲把我紧紧揽在怀里,听我诉说刚刚发生的事。末了,她说:“人家说疯子咬了人,跟疯狗咬了人一样,会传染。马爱娥神叨着呢,你可得离她远一点。”等父亲从工地回来,母亲揭开锅盖,把留的面条端出来,又把油泼辣椒和醋壶端给他。父亲一边吃,一边听母亲在旁边唠唠叨叨。母亲把我被马爱娥吓着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母亲说:“那个疯子,不知道怎么跑到瓦窑坡来了。可别让她把孩子给咬伤了,人都说疯病会传染呢。”“你又听胡说八道呢?”父亲笑了,扒拉了几口面条,“我听说过狂犬会传染,还没听说过精神病也会传染。再说了,马爱娥得的是癔症,又不是精神病。”父亲吃完饭,母亲把碗端走洗涮去了,又给父亲端来一大茶缸酽茶。父亲呷了一口,脑袋来回轻轻地晃动,把浮在上面的茶叶吹开,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啜饮,“我这些天在齐家楼工地上听人说,马爱娥其实也是个可怜人。”他说。三十多年前,马爱娥也是一个良家妇女。她十七八岁时从外地嫁到了齐家楼,男人是个窑匠,活干得仔细、出彩,人却老实,只挣自己该挣的那一份钱,心不黑,请的人就多,渐渐地连沟对面的赤城乡都传遍了。每年正月初五一过,来请箍窑的人把门槛都踩平了。正月里在家不出门,订单就已经排到了四五月份。上天为你打开了一扇窗,也许就顺手关上了一扇门。马爱娥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别人看着眼红。但有一样别人不眼红,这话慢慢地就传到两口子的耳朵里来了,“就算他们有十万,一百万,死了也带进棺材里吗?一个箍窑的棺材瓤子,还是个断种子”。这话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两口子结婚眼看也四五年了,马爱娥连个土豆都没生出来。没办法,只好抱养了一个女孩。“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样红。”马爱娥的好日子突然间就到头了。那年夏天,马爱娥的男人在赤城给人挖窑洞,窑塌了,男人被结结实实地压在下面,死了。马爱娥哭了好几天,哭得死过去好几回,醒来又接着哭,那能有什么用?死人也没办法活过来。她娘家人都死光了,婆家也没有老人和兄弟,邻居帮衬着把人埋了。自那以后,马爱娥就有点神神叨叨,日子过不下去,但为了一张嘴,再难也得往前走。经别人说合,她拖着两岁的孩子嫁给了外村一个四十多岁的光棍。光棍也不学好,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家里只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都说人越没有本事,脾气就越大,气性也跟着大,受不了苦,忍不了气。他把别人用来挣钱的气性都使在脾气上了。男人给家里拿不回来一分钱,回家还样样都看不顺眼,动不动就拿马爱娥和小女孩撒气。日子就这样又凑合了十几年。谁知道这样的男人阎王爷也稀罕。那一年,半夜里来了个贼,到处翻,翻不出个值钱的东西,就在灶房顺手牵羊拎了半壶油,刚爬过墙头,这个死男人半夜里输光了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一看墙头上爬过来一个贼,他正没好气,冲过去跟人家扭打在一块儿了。他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哪里能打过一个翻墙上房的贼?也是他该死,抱着贼的腿就是不放手,又扯着嗓子喊抓贼。农村的住户比较分散,邻居家隔得也远,又是半夜,人家睡得五迷三道,谁肯爬起来抓贼?贼却心虚害怕了,背后摸出个铁家伙,照着男人脑门就敲了两下,马爱娥的男人手这才松开。贼跑了。等到马爱娥听见动静,穿着衣服跑出去时,男人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一个家庭,男人、女人、孩子就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无论少了哪一个,生活都不够完美,家庭也会失去平衡。别看就那么一个不成气的男人,活着的时候是这个家里的累赘,他一走,这个家也就散了。马爱娥是外乡人,男人死了,自己拖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没有娘家可回,早先男人的家也是别人的了。这边男人一死,村里有些不正经的半大小伙子、光棍老汉,有事没事就爱往门上踅摸。马爱娥一气,一急,精神上就又出了一点问题。这样好歹撑了一二年,家里只有出的,没有入的,两个女人干瞪眼,除了干仗就是哭天喊地。实在熬不下去了,马爱娥托人说合,给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这个家才算没有垮。家安稳了,马爱娥的癔症却一阵好,一阵坏,一个月总要发作那么几天。发作的时候,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女儿女婿不得不由着她。后来,也不知是病加重了,还是她看这招管用,故意装疯卖傻,瘟病改成不定期发作,而且还比先前增加了花样,她韶刀病一犯,还爱把女儿女婿房里的事往外说,添油加醋,说得五彩缤纷。女儿骂不管用,女婿脸没地搁,把她摁在家里打了一顿。凡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二次。马爱娥记吃不记打,女婿一打她,她到外面更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有一次马爱娥被打得受不了,就跑了。一跑出来,就没法回去了。她就这样成了过街老鼠。农村人过日子,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父亲说,“自己过着太平日子,也别笑话人家不太平。”父亲叹了口气,把茶喝完,刷完牙,洗把脸睡了。马爱娥果然是一路要饭,走街穿巷,一直走到我们瓦窑坡。她们家附近的几个村,她都要遍了,没有几个人再肯赏她一口饭。也是,她又不缺胳膊少腿,干吗非得要饭呢?瓜宝升和疯天社还时不时去给人打零工挣零花钱呢。有一天下午我自己在家,有人摇门。小白汪汪叫着冲出去了,对着门外咬个不停。母亲出了门以后,我就按她的吩咐把门闩上了。我扒着门缝一看,疯子马爱娥也扒着门缝朝里觑呢。她笑嘻嘻的,露出一口黄牙,隔着门就闻到了一阵馊味。“给我一个馍吃。”她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进屋,拿了一个馒头,从门槛下面给递了过去。她接过去,说:“我想进来喝一口水。”我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我说:“我妈说让我离你远一点,你再不走,我就放狗咬你!”小白听懂了我的话,前爪搭在门上,呲牙咧嘴,“汪汪”地叫了起来。马爱娥吓得一溜烟跑了。我最后一次见马爱娥,是在老刘修自行车的摊上。老刘也不嫌马爱娥脏,给她拿了一个小杌子,倒了一碗水。马爱娥跷着二郞腿,跟老刘吹得唾沫星子乱飞,“你是个死老汉,我是个瓜老婆,咱们两个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般配着呢。”马爱娥说,“你收留我不吃亏!你别看我面黄肌瘦,我能吃能干,伸手能端起大老碗。我就一样不行——生不了娃。再说了……再倒一碗水……”马爱娥抹了一下嘴,从老刘手里接过碗,“再说了,人老了就得有个窝。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草窝窝。没有老婆的窝哪能叫窝呢?死狗还要在外面踅摸母狗呢。”老刘嘿嘿傻笑。左手拿着自行车内胎,右手拿着挫刀,还在不停地挫。“我给你讲个故事。”马爱娥把碗放在地上,“说是一个秀才找人算卦,问他未来的老婆在哪儿,他想先去看看。算卦先生就说在某某桥底下。第二天,这个人就跑到桥下去看,结果发现桥底下睡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小叫花子。秀才吓坏了,回去摸了一把刀,跑到桥底下,照着小叫花子的头上就砍了一刀,脑门上流了好多血。秀才吓坏了,把刀一扔,跑了。“后来,这个秀才当了官,娶了当朝一个大官的女儿。晚上入了洞房,一掀盖头,发现新娘子漂亮得不得了,他心想那个算卦的不是胡吹吗?他在灯下把新媳妇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越看越喜欢。美中不足的是,新媳妇眉心有一道疤。他就问媳妇。媳妇说,某年某月在天桥底下,突然来了个人,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砍了一刀,也是命不该死,恰好这个当官的夫人路过,把她给救了,一看她长得还挺标致,又认了女儿……老刘,人的命,前生定。你这辈子就该拾一个要饭的老婆……老刘……””马爱娥突然尖叫了一声,“你把人家的车胎挫断了……”老刘停了手,脸刷地一下红了。老刘补的是村委会吴主任的自行车胎。吴主任估摸着老刘该补完胎了,正好过来取自行车。一看老刘还在挫车胎,把车胎挫出一个大窟窿。吴主任的脸涨得通红,“老刘,你这个断子绝孙的死老汉,你把聋子治成哑巴了!”一看马爱娥坐在杌子上喝水,又骂:“你们这两个孤鬼,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呢?马爱娥,我正寻你呢,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你找我做啥呢?”马爱娥说,“你家里不是有老婆?你要不嫌我脏,我跟你也能成!”“你以为我是老刘,八辈子没见过女人?腥的、臭的都要!”吴主任搂起一个打气筒,劈头就打马爱娥,“你赶紧滚回你们齐家楼去!你死也给我死在齐家楼,你要再跑到我们瓦窑坡来捣乱丧德,我不打折你的腿才怪!”马爱娥跑了有十几步远,看吴主任不追她,嘻嘻一笑,“你一个烂妇女主任还算个官?你算个逑官!你少操我的心,你把你们村里婆娘尻子的心操好就烧高香了!”吴主任气得又拎着打气筒追上去,马爱娥又往前跑了十几步,看见吴主任弓着腰,双手扶着膝盖呼哧呼哧喘气,又笑了,她唱了一段秦腔《五典坡》:“倚官携势你欺贫困,嫌贫爱富昧婚姻,说什么义来道什么信……”一边唱着一边走远了。马爱娥果然守信,以后再没有到我们瓦窑坡来。她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夜。等到天明被人发现的时候,马爱娥蜷成一疙瘩,已经冻成了一块石头,又硬又冷,扯不开也抻不直。她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都被野狗撕成了碎片片。枯守拙 谢谢大家鼓励原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fb/13710.html
- 上一篇文章: 琢玉作文班三四年级优秀作品选童话故事
- 下一篇文章: 宜禄风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