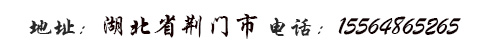07班故事人生优秀随笔
|
北京白癜风的权威专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目送 邹思言 这样的日子还要怎样过呢? 阴雨下他撑着一把灰色的伞,似乎也挡不住他脸上的忧愁。在受够了他的工作后,他终于要辞职了。 空中奔腾翻涌着厚厚的乌云,时不时传来沉闷的一声轰鸣。灰色的天,灰色的城楼,灰色的马路---这一切都是灰色的了。他丝毫不在意路旁青翠的迎春的藤,毫不在意马路上尖锐的鸣笛。他只是拖着两条颓丧的腿向前迈着,甚至连雨水冰凉地沁进鞋袜里也像没有知觉一般。 今天是回家看父母的日子,他还算是个孝子,公司离父母家近,每周下班后会顺路去看看。但今天不同,他站在熟悉的家门前时迟疑了许久。他低下头去将领带系好,揩揩肩上的雨水,又用手在憔悴的脸上狠狠地抹了下,然后敲了门。 这间不大且阴暗地的屋子是他长大的地方,几十年来这里像是时间停止了般什么都没有变。一样的布置,一样的摆设。刚一进门,一股暖气就将他包裹住。母亲在墙边支的小桌上摆了一桌的面粉,他知道,在这天做些面点是母亲的习惯。 没等他开口,母亲就招呼他坐下,递给他一杯热茶,开始嘘寒问暖。他也时不时瞟瞟坐在躺椅上读报的父亲,似乎没什么表示,只是进门时打量了他一番,又继续读他的报。 “儿子,最近过得怎样呀?工作忙我知道,可别把身体搞坏了哟”母亲一边把冻过了的包子往袋里塞一面说。 他局促地将两手在裤腿在搓了两下,“好着嘞,您放心”他心里一紧。屋里明晃晃的灯暖得有些不安,屋中暖烘烘的气流让他心里像哽了什么东西,急着要涌出来,他只好起身,忙着要走。 父亲瞥了他一眼,将老花镜“啪”地一声放在桌上,“我送你”。 三个字砸在他头上,让他不知所措。他知道父亲是个执拗的脾气,劝他也不中用的,便接过母亲手里的包子出门了。 一出门便是一股寒风迎面而来,刺得他脸上疼。父亲走在他前面,不紧不慢,他也只好不远不近的跟着,只见父亲那瘦小的黑色的背影在眼前一晃一晃,不禁感到父亲真的老了。二人一路无言,似乎都难以打破这坚硬的沉默。 狂风还在怒号,将伞吹得鼓鼓的,发出呜呜的声音,密集的雨点打在伞上,打得沉重,像沉重的鼓点打在他心上。路旁的树也因此被打得东倒西歪,一幅狰狞的面孔。 父亲在路口停下了:“我就送到这了,你自己到对面搭车”。 他没有出声,表示默认,带着满鞋冰凉的雨水,走到了对面熟悉的公交站。 他低下头去,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辞职信,又带着怨气地猛地塞进包里。这时他的伞略微抬起了一点,在风雨迷蒙中,似乎看到了什么--- 一个黑色的、瘦小的身影立在一片风雨中。狂风卷着大雨,接着一声雷重重地在他心上狠狠敲了一下,对面的黑色的、瘦小的影子一动不动的立着,一双眼仿佛在托举着这片风雨,寒风吹动着他黑色的围巾,吹起他银白的发---那是他大半辈子为儿女奉献的见证。猛然间,一波苦水涌上他的心头,苦的,酸的,甜的,霎时混在一起在他心里翻腾、回旋。那白发象一根根细丝扯得他生疼。他曾经高大、坚强的父亲也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磨得平整,瘦弱的,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了。 他慌忙地招手,示意父亲回去,而父亲很快也招了招手,然后背过身去,象没有看见般,留给他一个固执的背影。 车子驶进站了,将父亲瘦小的背影挡得严严实实。他飞快地爬上车,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车窗边,透过玻璃上密密麻麻地水珠,他看见,那个黑色的、瘦小的人仍站在原地,默默地注视着他的方向,一点点、一点点望着车子缓缓驶出站。而他呢?则是呆呆地、呆呆地看着那个黑色瘦小的人渐渐消失在窗尽头…… 他哧地坐下,脚下的雨水浸透了鞋和袜,冰得直穿心间,手边的冻好的包子依旧冰凉,可又怎会是冰凉的呢? 他终于,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两行泪沉沉的、静静的淌了下来…… 日子总还是要过的。 油滑 吴东霖 “游游,别睡了!”同事推了推午睡的游游,“来生意了!” “嗯?嗯——来了!”刚刚还哼哼唧唧的她突然来了精神。又可以耍耍嘴皮子拿钱了,她禁不住想,妈妈不知道最近看中了啥,钱要得多了,争取一次性满足她。 她冲向了柜台,“顾客您好,请问您是选眼镜吗?”她指指货架,“先选镜框吧。” 顾客拿起了一副宽边眼镜,“这款宽框搭配您文质彬彬的脸,书生气更重了呢!”游游自认为不失时机地解说了一句。 “银丝边框也不错,显得您眼睛大,更衬脸小哦!” “小框眼镜可以让您英俊的脸庞充分显露,帅气逼人!” …… 随着顾客的视线变化,游游熟练地切换着解说词。 顾客终于选好了镜框,游游深吸一口气,迅速把国产镜片介绍册收入柜台,抽出一本进口镜片介绍册,一边打开到最贵系列页面,一边开始介绍:“先生,医院的验光单,这个系列最适合您了,超薄、防蓝光、防起雾、防磨损、防……”“行行行,就要这款。”顾客的豪爽让游游心花怒放,“价格也不贵,加在一起,我跟您打个内部折扣9折,”游游压低音量,对着顾客做出了个噤声的手势,仿佛这个折扣是多么的不为外人所知,“再吉利一点,收您元好了。”“行!” “请问您贵姓?”“姓华。”“好的,您过一会儿来取吧。” 顾客走了,游游看着计算器上的数字,暗自欢喜。医院旁边开店就是好,有太多的顾客甘愿被宰。这单有元的利润,全部发给妈妈吧。 装镜,游游把一片普通镜片熟练地按入镜框,防这啊防那啊,笑话,不过是抬高价格的幌子罢了。“油嘴滑舌”就意味着丰富的“油水”!那吊牌上,明晃晃地写着:20**年*月*日,元。 交货给顾客,游游终于歇了下来,不如问问妈妈要这些钱做什么吧。信息刚发出不久妈妈就回信了,说自己眼睛不好使了,预定了一副眼镜。“妈妈老了,我也算尽孝了。”她心满意足地躺回小床上,“华先生真是好骗,”她心想,“每天要是多一点这样的顾客我就发达了。”带着憧憬,游游再次进入梦乡。 这次惊醒游游的是妈妈的电话。 “女儿啊,我预定的那副眼镜到了,它可太好了,可以治疗白内障,治疗高血压,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喂喂!你喘什么气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啊?那卖眼镜的华先生可好啦!整天管我叫妈!他公司的眼镜卖得可好啦,他特意给我留了最后一副,原价0,华先生给我打了亲人折扣5折呢,最后还优惠取了个吉利数,元!太划算了!我把图片发给你,看看,你妈戴上多年轻多好看啊!” 游游面如死灰,挂断了电话。 屏幕上,妈妈笑靥如花,鼻梁上架着的,赫然是她中午推销出的那副眼镜,那吊牌上,明晃晃地写着:20**年*月*日,元。 钥匙 全鹏寰 家中的酒柜中放着三把钥匙。两把已经生了锈,死气沉沉的,第三把则截然不同,迸发着无穷尽的生命力。 这一切都要从一年前说起。 我家是个世代酿酒的传统家族。几乎每个长辈都掌握着酿酒方法。父亲44岁了,已迈入了不惑之年,但仍然坚持着酿酒,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酒坊,坐落在小城的黄金地段。店内装饰一律为红漆刷墙,原木家具,暗黄色的灯光照在家具上仿佛上了一层蜡。店里的伙计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穿着土蓝布上打着大补丁的马褂,饱经沧桑的脸上顶着个大酒鼻。平日无顾客时便悄悄揭开那红布封着的酒坛,小酌几杯。小店客人不多,时常光顾的都是些念旧的老人,他们来这里重温上个年代的美好,对酒坊有着深厚的感情。 父亲的店客人虽少,但他对事业的热情可谓分毫不减。早九晚五,一天的工作就是在那巴掌大的小作坊里,一遍又一遍地加水,翻糟,蒸煮原料。尽管前来买酒的人很少,但我家酿的酒质量还不错。 在我的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父亲手中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它每次打开那扇大门时显得格外笨拙,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举着根痒痒挠去战场杀敌一样,力不从心。也许是因为自身有些真材实料,它氧化的速度还不算快。 哥哥24岁了,是中央财经大学刚毕业的博士,他一回来,看见父亲的店,总是痛心疾首地摇头,大声叹息,好像父亲干着不正当的营生,拍着额头长叹:“我滴个乖乖,这干的是什么事?白白浪费了这块黄金地段”。父亲听了之后,心中大不满:“有本事,你来露两手”,恰逢酒坊不景气,生意惨淡,于是,哥哥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事业。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哥毫不例外。第一把火烧向装潢:墙上贴满“moden”的海报,地板与天花板刷成黑白两色。酒坛收了起来,换上锃亮的高脚杯。第二把火:赶走穿土布衣的店小二,转身招来身着西装打领结的侍者与妙龄女郎。第三把火便烧到了门身上:他嫌原来的门太老旧与店内装潢不协调,直接换了卷帘门,因此钥匙也换了,原来生锈的钥匙被银闪闪的新钥匙代替了。从此,这座城中,一个怀旧老店消亡了,伴随着的是一个时代中心的崛起。 哥哥的经营模式十分新颖。首先他不再采用父辈们的酿酒工艺,直接用酒精勾兑成酒,省去不少工序和麻烦,其次,店中只有他一个人经营酒水,其他人则助兴营造氛围。最后,店中冷气与音响全天开着,这可不,哥哥成了缴纳电费的大户。没过几天我发现他那把银闪闪的钥匙开始生锈了。生锈缘由是没日没夜的冷风侵蚀?还是如同猛虎的开支?还是虚有其表的假象? 次日我便发现了真相:一位多日未来的老伯到了酒店门口,脸上带着些许不解与疑惑,最终他走了进去,只见他面红耳赤地与哥哥谈论,最后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见哥哥毫无表情地转过身去,往一只高脚杯中注入些少量酒水,还加了一片柠檬。老伯大惊失色,呆呆地盯着价目表,又看了看手中的酒杯,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从他眼中我看到了迷茫与不安......顿时我突然明白:这钥匙生锈竟是时间太快了。 终于,那把钥匙撑不住了,倒下阵来。 “我家的大博士也不过如此嘛!开了几天店?”掐指一算,“呵!十三天十一个小时吧!”父亲的话中带了点挖苦。“哼!你懂什么?我这些天赚的钱可是你同等时间赚的三倍!”戛然而止的理论。两人都望着彼此手上那把曾经熠熠生辉,如今黯然失色的钥匙,沉默良久,又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是太快吗?是太慢吗?是腹有诗书但垂垂暮老吗?是虚有其表但朝气蓬勃吗?到底是工匠精神的专一,还是积累资本的迅速?我未来得到第三把钥匙后如何抉择?会走父亲与大哥的旧路吗? 其实,这些答案只有钥匙知道。因为如今的第三把钥匙就是一、二把钥匙的各一半。也许那个晚上快和慢都有了抉择了吧。 病房里的母亲节 谢郭玟瀚 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了病,医院。病房里有一位年长的母亲,恰好,她们得的是同一种病。 年轻的见到年长的说:“太好了,至少不用孤零零的熬过这些日子了!” 年长的母亲应道:“是啊,我的孩子一周才来看我一次呢,现在终于有人陪我扯谈啰。” 年青的母亲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是吗,你的孩子多大了,什么工作呀?” “两个崽,都二十好几了,乡里娃,学也没上。大的一直在工地上打工,经常晚上抽空来看我。小的那个,攒了点钱出门去做点小生意,快半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真让人担心 ——你呢?” “就一个,比你的小一点,——考上大学了呢!” “那还不是你这个做娘的功劳!” “那是,早上鸡蛋牛奶、晚上一杯咖啡、天天有鱼有肉的,怕他营养不够呢。” “那他肯定很孝顺你吧?” “那还真是!我还记得他小时候就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对妈妈好,要给妈妈买房子买车子,天天给妈妈送花呢……一眨眼就长大了。” “哎,我那两个孩子,就没这么说过。也是,小时候他们吃都吃不饱,是我苦了他们呀。” 就这样,日历在两人不经意的聊天中翻过,中间年长母亲的大儿子也来看了几次,母亲节就要到了。 “真是期待呢,我那不争气的小儿子去了哪儿也不知道,这母亲节也过不出啥滋味来。” “哎呀,姐姐不要担心了!我还蛮期待我孩子的礼物呢,去年他就忘了,还说今年一定补上呢。” 两位母亲都满心期待。 母亲节到了,这天上午。病房的门就被推开了,一位面庞黝黑的年轻人拿着几束花,径直走到年长母亲的床头。 “娘,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几束花来表示一下心意……” “没关系,只要你惦记着的就好了嘛!”年长的母亲幸福的说。 正在此时,年轻人手里的手机响了。趁着年轻人转过身去接电话的空当,年轻母亲凑到年长母亲的耳边道:“你家儿子怎么这样,就买这么点东西给你,来看你了还有闲心玩手机!” 年长母亲刚想说话,儿子突然兴奋的转过身把手机递给母亲。“娘……弟弟来电话了!” “真的吗?”母亲忙接过手机,“娘,我现在在长沙做生意,给您报平安,现在生意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娘、母亲节快乐!”听着听着,年长母亲不禁热泪盈眶。 护士抱着一个大包裹进来。“是儿子的礼物吧,这么多!”年长母亲问道。 年轻母亲拆开包裹,是一大堆的衣服,上面还有一张纸条。 “哇!儿子送的新衣服,这么多,纸上写的是啥呀?” “母亲节快乐!妈妈。”不知怎地,年轻母亲突然哭了,她把纸条紧紧的攥在手心里。 但年轻人看见了,他一言不发。纸条上写着:“没有衣服换了,妈妈。” “火种” 王淳仪 “请X-A号注意,陆地今日最高温度:度。最低温度:-30度。已检测到。” “可活动时间为21:00一23:00或04:00一06:00。祝你好运。” 这是我毕业的第一天、也是我正式工作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是我真正踏上这颗星球表面的第一天。自18年前地球地表水剧烈干涸以来,地球就已向他的子女们宣布了无限掠夺的终结。 谁也没有料到恐怖主义、宗教活动、暴乱会来得那么快;谁也没有料到。这直接导致无数国家政府倒台;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最后的饮用水的来源——生物水。 代号为“普罗米修斯计划”的寻找水的世界级参与性计划就这样应运而生。联合国倾动了最后的各国力量将普罗米修斯们送进宇宙,寻找人类新的方舟。被基因筛选通过的天选者们将自出生起,接受联合国的密封式培养,直到十八岁,他们将接受毕业的第一份“礼物”。 这是他们的荣誉,更是他们的使命。 ——好吧,其实出舱前我内心压根没有“使命”这么宏大的想法,因为我太兴奋了——拜托,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自出生起就没走出过一艘飞船,第一次看到外部世界,不激动才怪!只是当我踏上这代号为Y-A的行星时,我的憧憬烟消云散了。 我想象中的外部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一望无际的灰白色沙尘,凹陷的沙坑上是小型陨石撞击的痕迹。我发射的地震波随着横波完好无损的被接收,我知道我不得不尽可能踏遍Y-A的每一寸土地。没有卫星,是啊,我只能如普罗米修斯般原始,但执著。 可勘测时间只剩一小时,我知道若现在返回舱室,那么曾走过的距离就成了前功尽弃,想起我的基因天赋,于是我继续向前、向前。“排除无水区,就是找到水的预召”我这样安慰自己。只是,时间结束的似乎更快一点,Y-A撕开它伪装沙漠的面具,变成狰狞而炙烤的火海,而我就在它的最中央。 探测服最先融化,成为黑色的小球。火舌卷上皮肤,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我的身躯,剧痛使我无法动弹,可我知道,因为我的特殊基因,我也如普罗米修斯般,不会死去。当我的细胞受到外在破坏时,它会立即分裂而新细胞依旧保持原细胞结构不变。因而当一个老细胞死亡时,已有另一个新细胞前仆后继,以让我一边死亡,一边重生,一边无比痛苦,一边还有能耐想着让痛苦死亡。 只是,寻找水源,让地球重生的意义,到底在哪? 也许对于那些来自地球的幸存者们来说,是为了那个星球上他们曾拥有过的幸福吧……湛蓝的天空、海鸥飞翔的大海、连绵的群山、互帮互助的人们。那些曾习以为常的简单,早已成为过往,成为他们宁可漂泊在孤独宇宙十八年所追求的一个幻梦,或者——仅仅是家乡情怀。 那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密闭十八年。忍受堪比死亡的痛苦与比死更痛苦的重生,意义又在哪?也许我也是在追求记忆里的一点东西、唯物主义告诉我的,不存在的东西。我总记得,或是其实不过是我觉得:我似乎理应在雪化后的草莓地上,与一位金发男孩跳起过海边小岛上的人们都会跳的舞;每当月光地下的草莓成熟,岛上的人们都会采撷草莓编成头冠;草莓节后融融的雪落在香杉树上,金发的男孩笑语晏晏。 是不是当我死亡无数次后,我们都可以找到那些记忆里的美好呢? 大海、雪、人们。 想着大海。Y-A的温度逐渐降低,我第二次出发。然后“死亡”。 想着雪,Y-A的温度再次退去,我第三次出发。然后“死亡”。 想着人们,-A的温度终又减去。我第四次出发,然后“死亡”。 ...... 不论是在什么时候,我总会找到的。 数不清是哪一次死亡,但这次我勘测到了水。 我闭上了眼。 当我缓缓睁开眼时,周围不再荒芜。我有点惊愕,直到身边朋友们一拥而上搂住我时,他们迸进我脖子里的泪才让我想起来: 已是地球水危机爆发一百年以后了,为铭记那些,为了寻找“火种”,他们忍受无数次肉身的溃烂与重构,十八年孤独的坚守,只为守护自己素未谋面的故乡的英雄们,人们在这一百周年重度推出了这样一个模拟体验计划。第一个尝试者便是“我”的原型——我。 设计者们导入了我父辈的记忆,那是初代漂泊者们。和我们这一代一样,他们是孤独的。和我们这一代又不一样,我们未曾生活在地球上,我们的血肉中没有地球人的那无可替代的乡愁,我们不懂过去的历史,我们没有雪、草莓、香杉树。而地球哺育了我们父辈的成长,地球是他们初尝自然生长的情感的地方。即使不过是为了雪夜的一场舞,因为那是地球啊,那是故乡啊,他们漂泊孤独宇宙,在所不辞。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采访我的体验感受,已一百一十八岁的我心中还是没有什么使命一类的词,鬼使神差地,我说:“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有想过,回到地球,我要在雪化后的草莓地上,与一位金色头发的男孩跳舞。” 远去的背影,别忘回头 尹子毅 常常,我们与父母心灵上的距离很远,很远;因为成长就是载着父母的目光前进,前进,但别忘了,给你初飞的力量的,是谁。所以,请记得回头,让温暖的目光隔空交会。 夜,缠满了高压电网般燥热不安;空气凝结成固体,吸不进去,呼不出来;窗外的灯火止住眨眼,街道强忍住喧闹,这是恶战开始前的压抑。惨白的灯光打在家里的餐桌上,我在一边,母亲在另一边。一场谈判,一场拉锯! “我不上这么多课外班,必须至少减一节,我需要时间休息!”榴弹震响着,炮弹呼啸着划过天际,可对面的堡垒毫发无损:“不行,这已经是最低限度了。” “大部分知识都在重复,有一部分学习不需要老师……没那么大的必要。”步兵坚硬的头盔和坚硬的脸庞步步逼近。“你不上课?那你做什么?你在你的同学中上的课已经是最少的了,不信你去看……,去问问……他们都比你辛苦!(原文)”对面的机枪吐着火舌,我的战士一个个倒下。 损兵折将,我的心中不解在呐喊,愤怒在暴动。在她面前,我的理由从来无足轻重。可这时,碉堡里传来轻轻一声叹息。“当初组班和家长们一起,中途退出去影响不好……” 影响不好!影响不好!我干脆一个也不去上!我冲回了自己的房间。 窗外,霓虹灯一盏盏地点亮了;行人,先是几个试探着走上街头,然后更多更多;汽车的鸣笛声传来。风,也轻轻掠过树叶了。如同战后的小心翼翼恢复生活,我心底的火也一点点熄灭了。门外传来一阵锅碗瓢盆的轻声,开始做晚饭了;这时,我才发现肚子饿了。 我慢慢地,回过头。心底的余热冷却了,而那声叹息始终在脑中回荡。 那天下午,接我回家的路上,一边穿过街道、马路,母亲一边给一个个别的家长打电话,一个个问能不能再加一个人一起上课,然后再打再问。夕阳都疲倦了,一步并做三步,想赶回到地平线下的睡床,我们还在路上,走啊走。 以前的每个晚上,母亲下班比我早一点到家,我就坐在书桌前胡乱地挑作业写,直到一阵诱人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勾着我的脑袋把我拖进餐厅,我便顺从这香味的指引开始吃晚饭。 回过头,我似乎看见许多曾经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似乎一路向前走,就一路忘记母亲在身后的支持与帮助。直到刚才,蒙上眼睛的我将从前的后方当作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我才发现自己以为掌握着真理,而实际懂得的却是如此之少。就因为从未回头,今天,我走错了方向。 轻轻推开房门,那阵香味又在吸引我了。是时候了,走上前去,道歉,再加协商吧。 “A林外史” 陈宇豪 8月2日晚 张钰晨坐在沙发上捧着手机。他要查成绩了。两个小时前,班级群里就一直没消停过,好学生一个劲的哭没考好,差学生则选择封建迷信。,请了一众神仙保佑自己。张钰晨属于前者,在群里几度忏悔,哭天喊地......所有人都在等着六个字母。能见到的几乎所有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齐盯着手机屏幕,一遍遍地刷新,似乎需要找到什么宝藏。三年前张钰晨进初中。那时他对“6A”不甚了解。后来中年班主任一遍遍强调,在他嘴里“6A”是努力,是善良,是成功的开始,是一切褒义词。考“6A”可以上四大名校,可以上““,“”可以找到好饭碗,可以走上人生巅峰。群里一张图片出来了,那是一位同学成绩。张钰晨根本无心点开看,他就想赶紧知道自己有没有考“6A”。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操作到倒数第二个界面,他停住了。“如果不是“6A”呢?”他问自己。“三年辛苦白忙活,到头来一场空。”屋外的风也停住了,树站在窗边正往屋里瞧着张钰晨。远方一片漆黑,就像没有“6A”的前途。张钰晨最终点开了,也看到了。———-他考了“6A”。一下子,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没有中举般的喜极而疯。“就这?”他用三年青春换来了一个“6A”。这竟让他失落起来。他试图回想起语文考试作文题目,脑海里却没有任何印象。倒是中年班主任说的“考一门,丢一门”又在耳畔响起。“该丢吗?”张钰晨想。这时母亲进来了。“我的好儿子啊!终于考到“6A”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她说。张钰晨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谢他。只见母亲转身,又发了一条信息给班主任。是为了统计“6A”8月3日没有考到“6A”的同学没在群里说话了。父母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一张成绩单。而没有达到学校指标的中年班主任被校领导谈话了。张钰晨不解。为这“A林”感到好笑。一转念,又感到悲哀...... 钥匙 周宇轩 小周和小邱是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成年之后,他们还是住同一小区。小周和他的女友住一起,小邱和他的女友小昱住一起。小邱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猫。 月底,小邱发了工资,于是邀小周去作客,小邱热情地款待了小周,他们一直和到很晚才散,两人都醉醺醺的。第二日,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小邱家的钥匙离奇“失踪”了,小邱和小昱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钥匙去哪里了呢?他俩一直想。过了一会儿,小昱说:“一定是小周昨天来作客时拿走的,除了我们,就只有他昨晚来我们家了。在你们开始前,我都看见钥匙在入门的柜旁。”小邱听完,立刻否认道:“不可能,小周不是那样的人,我和他从小玩到大,我了解他。”“呵。”小昱听了,轻蔑地一笑“人是会变的你不知道啊,还有小周女友生病了他现在急需用钱,谁知道他要是偷了钥匙会不会趁我们不在时来拿。不管怎样,你都去问问小周。”说完,小昱把小邱这个月工资连忙放入保险柜。 小邱出了家门,不一会儿就到了小周家门口。他向前踏一步,刚欲敲门,却停住了,面露难色,似乎在犹豫着什么,又退后一步,在门口踱起了步。忽地,门“吱呀”一声开了,小周手提垃圾袋,似乎出门倒垃圾,一脸惊讶地看着小邱。小邱见小周出来了,脸一红,双手从裤兜中拿出来又不知道放哪,只好放回去,“嗯嗯呃呃”支吾了半天,脸都憋成了酱紫色,冒出来一句:“天气真不错,你打算去干什么”小周奇怪得看了小邱一眼,似乎感到不解,提了提垃圾袋,示意去倒垃圾。小邱见了,尴尬地笑笑,搓了搓手:“倒垃圾啊,哦,挺好的。我没啥事,就是想说小区最近贼比较多,你最近经济比较困难,小心一点。”说完,小邱飞奔而去。 小邱一回到家,小昱就凑上来:“怎么样?”小邱没好气地说:“没问没问,真得太尴尬了。”小昱听了,脸色大变:“这怎么行!今晚他知道我们要出门,那家里不就……”话音未落,敲门声响起,小邱一开门,是换锁公司的师傅:“您好,是邱先生家吗?周先生付款给您家换锁,您看看哪种您需要?”说着,师傅进门时一不小心碰到了柜旁猫舍,猫舍被撞开一段距离,大家惊奇地发现: 一片钥匙静静地躺在那里。 故事人生:“喂?!” 刘璟瑞 “嗡……嗡……”他的手机拼命地摇动身躯,发出无声的呼喊,显然呼喊将他的思绪从电脑中拉回现实,墙上钟的指针停靠在“十二”处,“啧,谁呀,这么晚了还打电话?”他疑惑中带着烦躁。 卧室内很安静,除了吹着冷风的空调在低吟,就是时钟“嗒、嗒、嗒”的脚步声,虽说他是个无神论者,并立志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但在按下“接听键”时,有点害怕的他还是犹豫了一下。桌上摊开的是数学作业本,旁边电脑的显示屏上正映着新闻“嫌疑犯杀人在逃!”,不难看出,他还是个中学生。窗外,路灯沉默地亮着,街上也一片寂静,光亮之处,不见一道影子----也许影子都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喂,这里是吉良,请问哪位?” “……” “喂?你好?” “……” 电话那头依旧沉默,“恶作剧吧?真是的……”他挂了电话,又回“几何”的世界,父母长期在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更喜欢被“数学题海”淹没的感觉。隐约中他听到了一些声响,“什么在振动?”巡视四周,目光最终落在刚刚被他扔在床上的手机,他放下笔,“啧”皱眉,“谁啊,又打电话过来?”他定了定神。 “喂?喂?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些杂音,很模糊,像是有人蒙着头跟他说话,但尽管他努力去听,还是听不清。 “喂,谁啊,你找我什么事?没事就别再打过来了,这……这不好玩……”他的声音都有点略略颤抖。 “……,……,……”话筒那边依旧是一些模糊的杂音 “对不起,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他飞快地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床上,然后他几乎瘫在椅子上,“到底是谁呀?”他不安极了,尽管房间开了空调,他的手心还是沁出了汗,甚至感到了一丝冰冷,“不会是哪位女生吧”他有点调侃自己,想借此缓解下不安,但他知道自己几乎不太跟异性接触,这时电话又一次振动,显示屏上还是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在振动中轻微的移动,显示屏的光也显得格外诡异,他一把掀起被子把手机盖住,“最近应该没惹上什么事”他不安地站起又坐下,最后他跑到窗前,扯一般地拉上窗帘,然后轻轻掀开了窗帘一角,窥探玻璃外的世界,远处的大楼还有几扇窗泛出暗淡的光,但黑还是主角,他紧张的扫视这每一处光亮和黑暗,企图找到一些线索。 “咚、咚、咚”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在卧室外响起,他惊得几乎从窗边弹起,“谁?”他朝客厅喊着,没人回答,空调还在低吟,钟“嗒、嗒”的声音也格外响,他总感觉那些角落里的黑暗总在张牙舞爪,“也许是钢筋老化发出的声音吧”他这么安慰自己。 重新回到桌前,他继续对付那些题目,眉头紧锁,百爪挠心,显然他无心做题了,一番思想斗争后,他用微微潮湿的手指回拨了那个电话号码。 “嘟……嘟……”电话通了 “那个……不好意思,你好像打给我几个电话,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吗?”他几乎屏息了 “……哦,不好意思刚刚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走路时可能不小心打开了拨号盘,然后又不知怎么地拨了你的号码”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另一端传来 他熄了灯,倒在床上。他舒展着身体,似乎要甩开今夜的恐惧,“这样都能打到我的电话,而且听他的口音,大概也是C市的人吧,真是有缘啊”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在世界这张大网里,社会像是一条条的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姿态连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闭上眼,他翻了个身“这么晚了,那个人在外面干什么呢?”他又睁开眼睛。 一把吉他撑不起一个梦 李飞霞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立了一把吉他。吉他包是老款式了,很旧,但不破,看得出它的主人曾经很爱惜它。不过,它现在落满了灰尘。吉他在房间里并不起眼,但谭启总会望着他出神。他从不去碰它,好像一碰就会摸到碎了一地的梦想。 十几年前的夏天,谭启走出中考考场。他计划了三年,后来坚持了七年的梦想开始了。 谭启喜欢音乐,他最喜欢的乐器是吉他,最喜欢的歌手是那时很火的十辰于。初三毕业,他终于有机会去学吉他。 整个暑假,别人在学预科,他则痴迷于音乐。由于谭启考上了市一中,父母自然不反对他一时的放纵,但是,如果谭启的父母知道谭启想要组一支乐队,他们一定会反对。 谭启的吉他老师姓张,他认为谭启很有天赋,并且也很勤奋,谭启受到张老师的鼓励,更坚定他的梦想。“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一了呢?”这句话是谭启的座佑名。 高一入学,他在学校里四处打听,终于找齐了键盘手、主唱、架子鼓手,组成了一支叫“追寻”的乐队。“追寻”活跃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谭启把乐队经营是风生水起。 乐队的名气高涨,谭启的成绩却日渐下滑。终于,他的父母知道了。三个人的家庭会议,气氛压抑。父亲的劝导由语重心长变得歇斯底里。父母的一再反对与谭启的坚持,这场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高二,“追寻”解散。乐队的人大都忙于学习,只有谭启不务正业。一次月考结束后,他背着吉他回家。这次,这把吉他似乎格外的重,压得他迈不开脚,走不动路。乐队解散,考试失利,母亲的眼泪,父亲的责骂,老师的失望,同学们的好言相劝……但是,谭启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乐队梦。他坐在公交车上,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看着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结伴而行。他坐在公交车的单人坐上,看着琴,琴也看着他。他轻轻拍了拍吉他,小声说:“梦想还是要有的,我们两个会实现它,对吧!” 高三,谭启的吉他被父亲没收,他被迫学习。终于他踩着线上了一个一本大学。他松了口气。从父亲那要回了吉他,大学四年凭借一把吉他和一个新的乐队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不过,大学四年一事无成,队友各奔东西,新的乐队又解散了。 22岁,谭启的乐队梦彻底地碎了一地。他必须要步入社会,一切都要靠自己,父母年纪大了。依靠了父母二十多年,他必须要让他们老有所依,生活的压力一下子砸在了他的身上。 大学学历,身无一技之长,找工作处处碰壁。父母低声下气帮他到处找关系,求了不少人,总算有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如今将近30岁,他有了一套90多平的房子,生活不算艰苦,父母也没再为他受苦。6年,谭启没再摸过吉他,只不过偶尔谭启还会听十辰于的歌。他深深的知道,一把吉他撑不起一个梦。一个梦想要与现实接轨才能有可能实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jb/13665.html
- 上一篇文章: 专筑匠心,质造未来蓝光发展举办首届工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