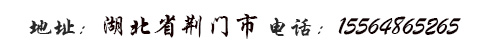岁月之痕,作家靳德信怀旧之作
|
治疗白癜风的偏方 http://m.39.net/pf/a_4698007.html 一 童年岁月 "哎哟,疼死我啦,哎哟……"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在做梦,梦见自己赤脚在街上闭着眼睛倒着走,忽然踩在一只鞋钉上。清醒之后,童年生活中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涌上心头。 听父亲说,我一生下来不象个人样,瘦得不足5斤。让隔壁大妈开奶后,等了三天母亲还是没有奶水。第四天父亲用毯子把我包起来,送给了离村5里地的刘姓人家。伯父知道后,连饭也顾不上吃,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对父亲说:“你还是个男人吗?怎么能把孩子送人呢?”“老婆没奶,我有啥法?”父亲说。“没奶咱们想办法,好歹孩子是咱靳家的骨肉,你怎么这么狠心呢?”父亲想想也是,当天黑夜,父亲又把我从刘家要了回来。 为了把我养活,父母亲决定给我雇奶娘。可是家里穷得分文没有,只好变卖一些家俱什物。正好本村有一个与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人前几天生的孩子夭折了,便成了我的奶娘。奶娘虽已有两个孩子,对我仍视如己出。奶娘奶水也多,没几天我就变得和正常孩子一样了。 奶娘奶了我不到半年,家里该卖的东西都卖完了,父亲再拿不出工钱了,只好又把我抱回家,母亲每天就用小米面糊糊喂我。我一哭,就叫邻近的婶、大娘奶上几口,几天工夫我又瘦了下来。后来还是伯父借给十几元钱,买了一只母山羊,开始用山羊奶喂我。我是靠吃山羊奶长大的,所以我每次见到山羊,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 我浙浙长大了,到了能记事的年龄,母亲常常领我到奶娘家去,并带上些小礼品,奶娘见到我很喜欢,一个劲儿地亲着,抚摸着,和母亲说想让我多在一天,可是母亲从来不让我在奶娘家过夜。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长大后才体会到了,那是母亲舍不得我离开她。 母亲一直担心我长不大,就捏了个泥人儿,领我到村里的奶奶庙,把泥人儿放在神象前,说:“我给奶奶送来我儿的替身娃娃,别让病魔灾难上我儿的身子!” 后来母亲又给我留了个“后坠坠",即在后脑勺挽个辫子。人们说这是娇养的意思。可在玩耍的时候,小伙伴们常常揪我的辫子,拿我取笑,我十分气恼。 我最不喜欢的是套在脖子上的红圈子。那是母亲用红布包着生我时的脐带做成的,名叫银项圈,人们戏称"狗脖俏"。母亲说到了十二岁才能剪断扔掉。 每当我出街和伙伴们玩耍的时候,母亲就很不放心,隔几分钟就上街找我,“丑时……丑时…"(我的乳名)一个劲儿地叫我,生怕我走丢或被孩子们欺负了。 食堂解散后,每人分得的口粮很少,人们把高粱壳、玉米轴、谷飞糠等掺进粮食里,再添上碾烂的榆树皮作筋料充饥。常常吃下饭却便不下来,我就随身带着芨芨棍,难便的时候自己往出掏。到了秋后,我常跟着父亲到碾过庄稼的场面上拾粮食,捡到的无论是高梁颗、还是玉米粒就扔到嘴里吃下去。最好吃又好咽的是黄豆黑豆。 母亲一向体弱多病,加上生活困难,病情日益加重。父亲省吃俭用,请医生给母亲看病,也没有治好母亲的病。在我九岁那年,母亲终究未逃脱疾病的折磨,撒手人寰了。 母亲去世时,我的祖母还在,我们祖孙三代便在一起生活了。祖母双目几近失明,不能料理家务,家里所有的活儿都由父亲一个人来做。父亲笨手笨脚,不会做针线活儿。所以,我从小学会了自已洗衣服,补衣服。 过年时,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我只能把旧衣服脱下来洗干净继续穿。记得有一年棉主腰脏了,我想拆开洗洗,原打算自已缝,却怎么也缝不了,父亲只好拿去让邻居大妈给缝。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季,我没鞋穿,常常赤脚走路,有时穿本家哥哥替下的破鞋,不是露脚指,就是鞋底穿了洞。一天我和伙伴们在街上玩耍,赤脚走在巷头的草丛里,忽然左脚踩上蒺藜蛋(菠菜籽状,有针),我赶紧用右脚支撑身体,结果右脚也踩上了。马上蹲下,手一托地,双手又沾上了蒺藜蛋,疼得我尖叫一声,流出了眼泪。慢慢一颗颗取下,一共有15颗。那次经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还经常做那样的噩梦。 第二年秋季,父亲带我到本村小学报到,我既没有书包也没有文具盒,只带了一支铅笔和两个本本。老师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丑时",老师说:"我问的是大名。"父亲说:“他还没有大名,我也不会起,老师给起吧。”老师想了想,说:“就叫靳德信吧,怎么样?"“好,好"。其实父亲是个文盲,哪懂得好不好?"好"只是随口说的。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学名,沿用至今。 在小学的几年,平时学习老师也不怎么督促,父亲也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可我认真好学,学习成绩一向不错。记得三年级写的日记、作文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念给同学们听。要写仿了,我只有几张小麻纸,还是我捡麻绳头,废铜烂铁卖了钱买来的。毛笔、墨、砚台、仿引都没有,只好等同学们写完了借着用。笔画多的字,独体字,哪个字难写我就在写过的作业本背面练习好几次。仿写好后,又在红线上加了小字。所以我写的仿常常多中"红圈",老师给贴在后黒板上,让同学们看。下午放学时留了家庭作业,可是家里没钱买煤油,不能在家里做作业,只好到隔壁大妈家去,由于大妈家的孩子与我同岁,又在同一个年级,我去了他们都不讨厌。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高小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阳高一中(初中)。然而文革开始了,阳高一中应届初中毕业生没有离校,学校自然停止了招生,我白高兴了一场。 二 青春记忆 我的青春经历是坎坷不平的。 高小毕业第二年,公社所在地下神峪小学增设了“戴帽初中",我们村同届的高小毕业生便到离村十里的下神峪学校就读初中。近60个同学在一间不大的教室上课,十几个外村的学生挤在一间黑洞洞的“牛槽窑"就寝。半年以后,初中普及了,村里也成立了初中,我们又回到了本村上学。 就近上学,既不用跑路又能省下伙食费,按说是好事。然而,办学条件更差,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是用麻纸糊着的。眼看进入冬天,教室连火炉也没有生。课本只有语文,数学和一本工农业基础知识。教师多是"民办"和"代课"的,有的刚刚初中毕业,有的连初中也没毕业。我们每天不是听老师念文件,读报纸,就是开“讲用会",批判会,排练文艺节目,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表演。 上午提前半个钟头就放学了,两三个人一组,拿着从黑板上抄下来的字条,到各家各户宣传,念两三遍了事。夏天,每天下午上完一节课就到野外打晒草,叫做勤工俭学。有时帮助生产队干活儿,间谷苗玉米苗,锄大垄田,如果遇到干旱,学校就组织我们抬水抗旱保苗。秋天,一到农民忙不过来我们就帮生产队收割庄稼,拾丢了的谷穗黍穗。秋收完了,再到地里砍茬子,准备过冬生炉用。冬春两季上学放学时,学生们个个挎着粪筐,拾粪积肥。一个学期下来,上课时间不足规定时间的一半。平时老师在教学上抓得不紧,对学生管教不严,也不留家庭作业,更不考试。所以我们在学习上一点压力也没有,很轻松,每天无忧无虑,十分自在。 特别是夏季,下午放学后太阳还很高,回家一放下书包,就拿起筐子和镰刀,几个同学相跟着,到村外割兔草。走到几丈深的山沟里,高高吆喝几声,"哎……哎……,你们在哪里……"等待着回音。割一会儿草,玩耍一会儿,打打闹闹,啍几声小调,说几句俏皮话,筐子满了,天也快黑了,回家时,已是头顶星星了。 初中毕业了,各公社又都成立了高中。不用进县城念了,大人们都认为是件好事。然而,所谓的下神峪高中学校,连最起码的学生宿舍都没有。我们外村的学生只好在村民家借宿。有的人家离学校很远,每天要走很多的路。老师没有办公室,和小学老师挤在一起备课,批改作业。教室不大,光线不好,破烂不堪的纸裱仰城在头顶上忽悠着,不时有泥土等东西落在脖子上,凉嗖嗖的。桌凳断腿的、缺角的、裂缝的,东倒西歪。我们不得不在村外自己建校舍,春天抹辋墼,夏天碹土窑,年龄较大的还能咬着牙坚持下来,年龄小的和女生们实在受不了那样的重苦,叫苦连天,唉声叹气。 秋天,我们总算搬到了新校舍,虽然八九个同学睡在一条顺山炕上,有点挤,但比在老乡家住强多了。 为了解决伙食费和学杂费,我们前后三次,共天在大同十二矿、周士庄铁路上打工挣钱。 学校的伙食比在家里好。入学前就把自已应分的口粮卖到粮站,又返还到学校,再加上国家补助,每人每天一斤一两粮,粗细粮搭配。最好的饭是一星期的两顿馒头,有的同学领到后舍不得吃,拿回家分给父母或弟妹吃。 课本仍和初中时一样,不分物理化学,只有一本工业基础知识,没有外语,更没有实验器材。语文老师是个老牌初中生,学历不高,但知识渊博,特别是讲古文古诗,枯燥的课他能讲有声有色,津津有味,同学们都爱听。数学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口才好,表达能力极强,同学们一听就懂。不过,那些年学校还是不怎么抓教学,老师只管讲课,学生爱学不学,有的学生有些课听不懂,就爬在课桌上睡觉。从开学到毕业,竟然连一次考试也没进行过。按说学制是二年,算下来真正上课时间是九个月。能学到多少知识就可想而知了。 高中毕业了,有门路的同学有的参了军,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公社"八大员",我没有门路,只好在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由于我老实可靠,生产队长让我当记工员,白天领着二十多个女劳力在旱水库干活,晚上汇总出工情况,第二天向队长交帐。同年夏天,公社要从我们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一批民办教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了第一批录用对象,被公社联区分配到本村学校任教,时年二十岁。当民办教师的报酬是每月生产队给记三百个工分,七元生活补助。待遇虽然不高,可我心满意足了,之后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不必说,每月还能见到现金。别小看挣那七元钱,在那时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呢! 到校上班的第一天,我穿的是一身褪了色的补着补丁的蓝衣服,一双煤溜底实纳帮家做鞋,其中一只露出了脚趾。一进教室,学生们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有的笑出了声。我知道笑的原因,但装作若无其事,避开同学们的眼光作自我介绍。月底到了,领到的第一个七元,首先买了一双黄秋鞋,后来发下几个月的工资又买了一身新衣服,也算武装了自己。 那个年代,到了十八九岁就开始谈婚论嫁了,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校期间就订了婚。二十出头的我也萌发了娶媳妇的念头。可就当时的家庭状况,庄户人家,光棍父亲,三间土窑,烟熏得黑洞洞的,炕上的蓆子黄黑相间,用白布补着补丁,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俱也没有。自己虽然是个民办教师,说到底还是个不拿锄头的社员,所以连个媒人也没有。我琢磨着,等靠媒人成家那是遥远的事,必须另辟蹊径。 我接的是个七年级(初二)班,三十多个学生,男女对半,不少女生已发育成大姑娘,有的只比我小两三岁。半年的师生相处,发现一个叫淑珍(化名)的女生脑筋灵活,学习挺好,相貌也不错,父亲是生产队小队长,她姊妹六个,四女二男,她为老二。在我看来,各方面都好,将来能成为伴侣再好不过了,便暗暗喜欢上了她。但作为老师又不能表露出来,只能做点不被人怀疑的小动作,暗示对方。如给点学习资料啦,课堂上多到她跟前辅导啦,作业批改的细点啦,劳动时找点轻活啦等。久而久之,却被学生们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开始风言风语,甚至传到村里人的耳朵,后来淑珍也觉擦到了,但我没看出她有什么反感。 到了年底,这个班毕业了,淑珍在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村主任听到我跟淑珍的事就想给我们当红娘。由于常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村主任以开玩笑的语气探试淑珍有没有那个意思,可淑珍说是没的事,但我听说过有不少人给淑珍介绍对象,她一个都不相不看。几个月过去了,我也不好意思找淑珍说出心思,只打听她找对象了没有。后来我也想通了,这只是单相思,点着的香火一头热,应该理解对方的心理,一个民办老师有啥出息?嫁给我还不是一辈子受穷?反正年龄不算大,找对象的事以后再说吧。 年夏未,大中专院校要招生了,上级给下神峪公社分配了八个名额。按照有关精神,生产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县文教部审核批准。招生对象必须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我高中毕业已有二年半,条件自然够格,但够条件的人全公社多的是,狼多肉少,竞争激烈。谁都知道毕业后就有了铁饭碗,一般人想也不敢想,我是怀着侥幸心理才报了名,在志愿书上填写了"朔县师范"。俗话说,借米丢不了半升,最多白忙乎。由于我常常帮助蹲点干部下户做调查,写典型材料,整理村史等,以村里的不正之风为题材写小评论,发现好人好事写表扬稿,极时送到公社广播站。村干部和公社书记主任对我有了很深的印象,评价挺高。也许是这个原因,大队和公社的两关都顺利通过了。 是年9月,我如愿以偿,接到雁北朔县师范的录取通知书。 (二年后,我终于和淑珍走到了一起,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三 师范生活 接到朔县师范通知书的那天,我是何等的高兴!高中毕业后,能够继续读书,再长知识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二年之后就能成为一名众人羡慕的公办教师了。 9月15日,吃过早饭,我告别家人,背着行囊,徒步到离村10里地的古城村,坐客车到了阳高火车站,上了火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别提有多兴奋了!列车飞快地行驶着,透过玻璃窗我望着沿线的风景,一切都感到新奇。一会儿想起父亲的嘱咐,一会儿想起好友的重托,一会儿又想象着学校的美妙生活:明亮的教室,舒适的宿舍,可口的饭菜,幽雅的环境………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12点多。 朔县火车站到了。出了站,发现有不少人扛着行李,拿着卫生用具,与我同路,才知道他(她)们也是到朔师报到的。上一届的几个同学早已在车站广场迎接我们,我们径直走向写着"朔县师范"的红色门旗的地方,坐上了学校的绿色大卡车。 踏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上毛主席的题字:"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进入林荫小道,拐过几个弯儿,穿过半个校园,我们终于找到新生报到处,班主任老师已在门外等候着。 报名后,老师们领着各自的学生认宿舍。我们的宿舍在校园的最西边,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约有十五六间。一进宿舍门,我就傻眼了:两条顺山土炕,中间是一米五、六宽的过道。炕沿是水泥打的,并不光滑,炕帮是砖砌的。两条炕各有一个已经生了火的地灶,不时有烟冒出来。地上有洒过水的痕迹,没有尘土,显然是刚刚打扫过的。玻璃窗户破了一孔,用麻纸补了补丁。每条炕上铺着两块旧苇蓆,有几卷行李靠墙放着,是提前来的学生的。墙围上贴着天蓝色的落花纸已经褪了色,有不少小坑,几处还脱了皮。老师说学校条件不怎么好,一条炕要睡七个人,有点挤,凑乎着住吧。 笫二天上午,学校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从七个县招来的名新学生,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静听着校领导讲话。会后各班同学跟着班主任老师去认教室。教室挺高大,也宽敞,但玻璃窗空不大,光线不够充足。白里泛黄的墙壁上贴着"学生守则“和几张宣传画,窗户以下的墙壁露出了泥皮,条砖铺的地坑坑洼洼,摆着五排黑色的双人桌,桌面有不少刀痕。这与我之前想象的相差甚远。听老师说,这房子是过去洋人作教堂用的,是德国人盖的。有的老师侃调说,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呀!后来又听说学校所在地原叫"米西马庄",解放后改成"新安庄"了。 更使我想不到的是,入学后并不上课,而是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教育也要学大寨"。上下两届学生连同老师共七八百人每天在校院南面的四五十亩地里平田整地,打埂筑坝,地里插着一块块木牌,上面写着"普及大寨县","苦干实干拼命干","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标语。喊夯声此起彼伏,说笑声不绝于耳,一派战天斗地,热火朝天的景象。各班分组,每天都有任务,打土埂不但要结实光滑,还要水平笔直。最后由学校临时领导组验收,如不合格,还得修理。 劳动两周后,学校要从招来的新生中,抽出50名有音体美特长的同学,组建一个音体美专业班,方法是自愿报名,任课老师出题测试。测试第二日我便成了音体美专业班的一员了。之后每天继续平田整地,我们班的任务都完成得又快又好,特别是我们组有几个细心同学把关,任务不但提早完成,而且质量第一,多次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休息时,我们班的气氛更活跃,有的唱歌,有的跳舞,五个一群,八个一伙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红歌。特别是学著和瑞芳演唱的《兄妹开荒》,向凡与淑琴演唱的《夫妻识字》,玉珍同学清唱朔县大秧歌,表情自然,动作到位,大家不断鼓掌喝彩,同时吸引着其他班的同学也来看热闹。 到了晚上,各班学生谈心得写体会,总结劳动经验,写战地生活报道,文稿由班长送到学校广播室或文印室,写的好的有的广播了,有的登在油印的《朔师小报》上。我写的稿子曾被选中几次,心里还美滋滋的。 连续六周的田地劳动,学生们的脸晒黑了,手磨破了,体重减少了,不管心里怎样想,嘴上从未叫苦说累,还露出喜悦的神情。正如有的同学所说,通过劳动,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改造了思想。 伙食也不是我到校前想象的那样美好。饭厅就是举行开学典礼时的大礼堂。冬天开饭时,蒸气笼罩了整个饭厅,灰蒙蒙的,象起了大雾似的,连对面的人也看不清眉眼,一顿饭往往吃着吃着就凉了。饭分组打,每10人一组,轮流值日。早饭是三两小米粥就盐胡萝卜丝,午饭是四两玉米面窝头,熬山药蛋和白菜,有少许木薯粉,难得看见油花,每人仅有一勺头。晚饭是一两米稀饭二两面窝头。唯一的好饭是一星期的两顿馒头,但吃不饱。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就到村里再买点吃的。这样的伙食标准女生们基本上能吃饱,男生们大多数不够吃,有时晚饭后和附近的村民买些黄瓜西红柿作添补。有几个同学半夜饿醒了,就偷了学校种的玉蔓菁吃,被学校领导知道了还挨了批评,记了过。 学校红委会每两周进行一次宿舍卫生大检查,要求学生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褥单洗得干干净净,卫生用具摆得整整齐齐。大多数同学都是花被面,花褥单,叠好后又苫着一块花枕巾,方楞四角。而我的被子是用过多年的红色被子,早已褪了色,和死马肉的颜色差不多,红不红紫不紫,褥子是奶奶用过的灰色毯子包了几块乱羊皮做成的,别说有花褥单,连白的也没有。枕头是用一块旧蓝布缝了个袋子,装了秕谷做成的。这和大伙的行李很不协调,减弱了整个宿舍的美感,影响了全班的等级,本该是红牌的“优",结果成了绿牌的“乙"。一名班干部对我说:"德信,你最好把行李换一换"。一句话触到了痛处,我非常生气地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钱呢?”由于被子棉花薄,尺寸小,在寒冷的冬夜里,我有好几次被冷醒。 再说我们的教室,冬天只生了一个不大的铁炉子,炉子周围的同学不觉冷,而其它地方特别是前后门跟前的同学,上课时冷得浑身打哆嗦,说话牙齿咯咯响,写字戴着棉手套,尽管御防着,有几个同学的手还是被冻伤,流了浓水。 眨眼间第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都盼望寒假快快到来,与家人团聚,我却选择了留校(每班二人,只要男生)。因为留校一来能利用假期时间多学点知识,二来家里的茶饭还不如学校的好,特别是过年的伙食,听上一届的同学说吃的比平时好。因此在放假的前三天我给父亲写了封信,告诉家里留校的事。假期的伙食果然不错,午饭很少吃窝头,增加了米饭和黄糕,晚饭多是吃面条。过年的那几天,吃了几顿饺子,大烩菜改成了小炒菜,每顿饭管饱吃。我庆幸自己留校还是做对了,长这么大,家里从没有过这样的伙食。 那些年,学校没有考试制度,教师工作不紧张,学生学习没压力。上课前班长点名是个形式,如有学生旷课,老师睁一眼闭一眼。我们音体美班学生连正式课本也没有,每每上课时,是老师发给学生用油印机印的"活页"纸。尽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遵守校规,用功学习,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但同学们认真学习的不多,谈情说爱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且美其名曰"抓大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把大事抓住抓好了,将来就能建立个"双职工"家庭,一辈子幸福。我没有搞对象的念想,也不具备谈恋爱的头脑,更不考虑将来家庭怎样怎样,只图学好知识,毕业后有个胶皮饭碗,能挣工资,对得起父老乡亲就满足了。所以在校期很少参加班里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不管别人学不学,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各门功课。每天不到起床时间就起床,去教室弹风琴练指法,晚上同学们都休息了,我还在操场南面僻静的树林里拉二胡练弓法。星期日同学们大部分到城里买东西或逛街去了,我却趁着宿舍人少不受干扰,能专心画画,不是临摹便是写生。有时到美术老师家里画画,老师手把手教我。两个学期下来,我的人物素描画在全班数第一,水粉画也不错,其中一幅大型作品被学校美术展览馆选中。 更让我感动的是音乐老师靳翠芬,她态度和蔼,性格温柔,不厌其烦地教我乐理知识和弹风琴指法。在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音乐理论及实践知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当年经济困难,毕业时我只到靳老师家里告了个别,连个小小的纪念品也没给留下,感到很对不起靳老师。 每个学期,学校都要定期举行大型活动,表彰优秀班级和个人。无论什么活动,我们班总比其它班搞得出色。开运动会有项目冠军、亚军,歌咏比赛始终名列第一,美术展览我们班的作品最多,……。所以普通班的学生说我们班是"人才班",老师们的评价是"要强班"。 夏季的朔师校园是十分优美的,丁香树是学校的一大特色,每条小路的两旁几乎都有。那一簇簇的丁香花十分惹人喜爱,还未到跟前,一股说不出的香味便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还有那田字形的菜畦,井然有序地种着各种蔬菜,绿油油的,十分养眼。开花时节,蜜蜂和蝴蝶在空中飞舞着,盘旋着。通往操场的大路两边是高大挺拔的钻天杨树,操场的西面有杏树、桃树、李树等。放学后,同学们流连在树林间,有的交流学习经验,有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有的……。 最有特色的是柏树园。四周房屋错落有致,古色古香,象个偌大的四合院。苍翠欲滴的松柏树遮天蔽日,从空隙中撒下几缕阳光,落在身上,惬意得很。窗前种植的月季花,枝繁叶茂,五颜六色,很是耀眼。要是在星期天,女同学们清脆的歌声就从窗口飘了出来……… 光荫荏苒,二年的学业期满了。其间有苦涩更有甘甜,有烦恼更有快乐,有伤痛更有欣慰,有付出更有收获!我没有辜负老师的辛勤培养和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学到了不少知识。毕业晚会的第二天,我告别了师生,背着行囊,高高兴兴走出师范校门。 四 教师生涯 师范毕业离校后,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由于学的是美术音乐专业课,一心想到县文化馆工作,或者到县城学校当一名专职“小三门"老师。然而,当年的毕业分配原则是各回各县各公社任教,我无奈被县文教局分配到阳高县下神峪公社,一待就是三十六年。 开学后,我去报到。联区指导员分配我到本公社重点中学上神峪学校任教。翌日,我到学校上班。校长问我擅长哪一科,我说美术音乐都行。校长说:“眼下学校没有音体美教师编制,你只能代初中语文课。听联区指导员介绍,你的语文程度不错,想让你代七年级(初二)毕业班语文。"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学校只重视数理化语文这几门主课,音体美等副课只在课程表上出现,根本就不上那些课。师范二年的音乐美术白学了,我只得听校长安排,代初二班语文课,兼班主任。 好在我上高中时语文学得比较扎实,教初中语文课不怎么吃力。期末统考,我班的语文成绩在全公社名列第一,班均成绩第一。在当时特别重视考试成绩的背景下,我的第一炮打响了!得到了上神峪村学生家长的齐声叫好,我在全公社老师中也名声大震。 然而,当班主任不是我的强项,让我伤透了脑筋。近四十个学生,又有十五六个寄宿生,每天有不少锁碎事情需要处理,忙得我焦头烂额。最怕的是学生打架格言,双方都有理由,互不相让,一旦处理不当,学生就会记恨你。有个学生很不听话,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考试经常不及格,有时打零蛋,我怕他拉全班的后腿,影响班级名誉,曾劝他退学,他的父亲对我意见很大。虽然那个孩子并不记恨我,可那件事至今想起来还特别后悔。 那时候,多数老师上班都骑自行车。买一辆自行车至少得元,我月工资只有29.5元,家里又没有积蓄,买自行车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到学校十五六里的路程,只能步行。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开始走,到家后已是头顶星星了。星期日干完家务,有时已是傍晚,返校只能摸黑走夜路。 工作上,老师们都很自觉,生怕成绩上不去,请假的很少。那一年秋天,我家的三分自留地种的黍子已黄半穗,遭到冰雹袭击,爱人捎信让我请假拾黍穗,因联区快要组织统考,我没听妻子的话。由于家里粮食紧缺,怀孕七个月的妻子只好担着筐担到地里去拾黍穗。结果第二日流产了,我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那年中考,我代的那个班考住中专的人数在全公社七个初中学校最多。后来的两年,每次公社统考,我代的班级语文成绩都是第一,班均成绩在全公社不下前二名。所以上神峪村的学生家长和村干部对我有很高的评价。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我申请回村任教,仍代初中语文课,兼班主任,还有几节副课,工作更忙了,种地只能靠每天早起,放学后的时间去做。常常晚上在家里备课和批改作业,直到深夜。 年,在“普九”工作中,我帮助全乡搞宣传活动,利用课余时间给学校写标语,制版图,星期日再到乡中和各小学帮忙。工作负担虽然加重了,但得到了重用,我的才艺有了施展的机会,心里很高兴。 孩子们大了,到了上初中的年龄。可是上级为了整合教育资源,各村初中点已撒销了,全乡只有下神峪一个初中学校。为了照顾孩子的生活,我正准备和乡教委要求调到离村十里地的下神峪乡中,领导却先找我谈话,让我到乡中任教,正中我的下怀。 中学校长专门给我腾出一个宿舍,让我的两个孩子与我同住,在宿舍盘了灶台,配备了炊具、暖壶等日常生活用具,我们可以自己做饭,不在学校食堂起火。这样不但省下了不少伙食费,两个孩子又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更有了良好的学习条件。 二十一世纪初年,国家实行了乡镇合并政策,撤了下神峪乡,合并于古城镇,乡中自然被撒除了,我又回了村,代小学高段语文课。这时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靠我的工资入不敷出,不得不东挪西借,债台高筑,生活十分拮据。 年,中心校长看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照顾我不用在学校任课,到各学校指导美术音乐老师,写写标语,美化校园,设计教室后黑板图案等,有时也到中心校帮忙。学了二年的音美知识,接近退休年龄才派上了用场。 五 晚年快乐 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怀孕一个月了,想让我们老俩口帮她料理家务,以减轻她的负担。那时我正好刚办了退休手续,去女儿家一来帮女儿的忙,二来过过大都市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我知道这一去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要做好长期居住的思想准备。于是收拾了家俱什物,该送人的送人,该寄存的寄存,有些事情一时安顿不住就托付给左邻右舍,两天后就启程了。 到了女儿家,老伴儿有事可做,买菜,做饭,洗衣服等。我仍然是个闲人,吃完饭就在小区附近转转,看看那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听听小商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想逛逛公园,不知该坐哪路公交,走远了又怕迷路。虽然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却没给我带来些许快乐! 最苦闷的是说不了普通话,不便与人交流,走在街上和哑巴一样。但转念一想,来京是为了女儿,又不是为了自己,该忍就得忍着点。一次吃晚饭时,女儿问我:"爹,来了半个多月了,感觉怎么样?还习惯吗?"我说:"好…力…,还…行…"。女儿听出我的话外之音,明白了我的意思,也没再说什么。 三天后的下午,我正在家里看电视,忽听有人敲门。"谁呀?"“快递。”开了门,快递员递给我一个用蛇皮袋裹着的大纸箱,拆开一看,是一架雅马哈牌电子琴。原来女儿知道我上师范时学过音乐,会弹风琴,怕我在这儿寂寞,就在网上买了电子琴让我玩。我如获至宝,接通电源,马上试弹。虽然从未弹过电子琴,但我懂得弹法与风琴一样,只不过四十多年没弹了,手指疆硬,指法肯定上不去。同一首曲子,连续弹了十几次,感觉一次比一次熟练了。 在家里弹了一周,比较熟练了,我大着胆子提着电子琴到小区外的公园去,弹了几首七八十年代的歌曲。不一会儿,喜欢唱歌的人就围了一圈,跟着乐曲唱了起来,人一会儿比一会儿多,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轻的,也有上了年纪的。他们还伸出大拇指,说我弹得不错,问我哪里的老家。我想,他们说我弹得好是故意夸奖我,然而,对我确是极大的鼓励。 从那天开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每天上下午都到公园的小亭子弹琴,认识了不少人。原来小区周围有很多会唱歌的,拉胡琴的,吹笛子的,吹口琴的,吸笙的,弹月琴的等,只是我来的时间短还不了解这些情况。没几天工夫,就和大家熟惯了,几个玩乐器的自动成立了小乐队,相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好每天下午就在公园的小亭子里玩。我弹电子琴水平虽然不高,但在乐队里是唯一的键盘乐器,音准,节奏感强,过去的老歌我大部分能弹下来。所以歌友们都乐意我给伴奏。特别是来自湖北的一位名叫翠云的女歌友,她最喜欢唱《洪湖赤卫队》里的插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而这首曲子又长难度又大,别人都不会,只有我是熟歌,不看曲谱也能流利地弹下来。所以每次活动,翠云最希望有我在,我们合作的天衣无缝,可以说是一个精彩节目,观众们拍手叫好。一个男歌友说:"老靳,你怎不早来,我们这里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经他这么一说,我才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我弹琴不仅快乐了自己,还给大家带来欢乐。 自由玩耍了几个月后,社区有关负责人组织周围的音乐爱好者,建立了民乐队,在物业二楼腾出一间大房作为活动场所,每周活动一次。于是我们二十多个人每周四上午就在物业二楼相聚,唱红歌的,唱流行歌的,唱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的等等。原来他们并不都是北京市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与我一样,不是看孙子就是哄外甥,没事的时候出来共同娱乐娱乐。他们了解到我在师范是学音乐的,一首歌曲如有不懂的地方就向我请教,我也乐意当他们的老师。有的歌友不知道唱某一首歌用什么调合适,我就用电子琴给她们试调。所以我在乐队中是个主力队员,很受大家赏识。 半年之后,女儿生了个男孩儿。我早就盼望着外甥的出世。每当看到大妈大叔们推着婴儿车在楼下走来走去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象他们一样呢?因为我已经年过花甲了,还没见到第三代,现在终于当上了姥爷,怎能不高兴呢? 有了外甥,老伴的负担自然重了,我不得不分担一部分家务,除了做饭,剩下的活都由我来做。并常替老伴看孩子,推着婴儿车下楼底走走。这样渐渐的又接触了一部分人。原来同一小区有不少山西和内蒙人,不是给女儿就是给儿子看孩子。在异地见到老乡分外亲切,特别是语言相同的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内蒙商都县的,名叫拴友,与我年纪相仿。因商都与阳高相隔不到一百公里,语言相同,甚至方言也一样。更巧合的是拴友与我有共同的爱好,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还会画画,两人也有了共同话题,经常形影不离,他拉二胡我弹琴,我拉二胡他吹笛,成为很好的搭档。 老伴刚来北京时也很不习惯,自从外甥出生后,认识了不少同龄人。河南的,山东的,湖南的,她们的儿子女儿与我的女儿女婿又是朋友,所以相处得都不错,并结了干姊妹,按年龄老伴排行老三,四个老人常在一起看电影,逛公园,下饭店。 我自从接管了家务,不能整日玩乐器了,只有到周六周日才能玩,但每周四的集体活动还是照常参加。 孩子上幼儿园了,玩的时间又充足了,这时我已经不甘心在小区附近玩了,有时和伙伴们坐着公交车或地铁到离小区较远的紫竹院公园去玩。我既要带电子琴又要拿椅子,分量很重,歌友们就主动帮我拿,口渴了,有人给我买矿泉水喝。热了,有人给我扇扇子。太阳晒住了,有人给我遮阴凉。用他们的话说,“你是红人,重点保护"。 最使我开心的是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炎热的夏天,要举行消夏晚会;五一节、国庆节、元旦、春节来临前都要举办庆祝晚会,晚会前要经过多次排练,彩排。因我一来懂得些乐理知识,二来我弹电子琴节奏性强,所以大家都听我的指挥。偶尔我因事不能参加,大家都不高兴。每次公益活动后,社区就发给我们每个参演人员一些纪念品,纪念品虽然价值不高,但领到时总有一种成就感。 到了旅游旺季,我常常跟着朋友们到大型公园游览。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颐和园和故宫,不仅使我欣赏到优美的风景,还了解到我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还有鸟巢那奇特的造型,天安门广场那浩大的场面,都使我心旷神怡,大开眼界! 女儿要搬家到西三环居住了,我不得不离开众歌友和乐队朋友了。离别前一天,十几个要好的朋友举行了欢送仪式,在饭店请我吃了饭,我不胜感激。临行前怕伤感,我悄悄溜走了。 来到女儿新家,居住条件自然比原来好多了,可是环境却与原来不同,两个多星期没有遇到玩乐器和唱歌的人,只有跳广场舞的。我对跳舞不感兴趣,非常想念以前朝夕相处的歌友们,因而莫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 一天做完家务上街闲转,在水果店门前忽然听得一对老人在说家乡话,近前一问,原来是老两口,他们是阳高县罗文皂人,男人名叫王成。再一攀谈,知道还是同行,退休后就来到北京,已有十八九年,几次搬家后现与我女儿在同一小区居住,这使我欣喜若狂。更使我想不到的是老王竟然与我有着相同的爱好,无论美术还是音乐,但比我专业多了。之后我常到他家去聊天,他还请我吃饭。在偌大的北京市,再次遇到知音,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收获,前些天的失落感便烟消云散了。最使我欣慰的是在老王的指导下,我又学到不少书法知识。我在师范上学期间虽然也喜欢书法,却没有下功夫练习过,只是略懂一二。由于老王的耐心指导,半年时间我的书法有了明显的提高,把写的字或草书或行书发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jb/14175.html
- 上一篇文章: 山东普创目前最全的除草剂讲解赶紧收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