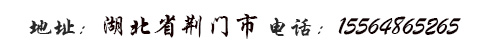我和他的年代,枪炮声盖过情歌
|
图片 微博 迷森鹿“我和他的年代,枪炮声盖过情歌,加密的电报里不能说一个想字,就连最后的告别,我都未能见他一面。”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在纸墨书香的浸润中长大。哥哥大我5岁。平日教我念书,夜里总去父亲的房里商量些什么。 每个睡不着的夜里,我总见他们房里的烛,燃至凌晨。 十五岁那年,时局变幻,动荡不安,护我长大的人们在我稚气的眼里也停不下衰老的步伐,而我的故园,在年少的我看来,从安定祥和到风雨如晦,所用的时间不过一朝一夕。 我在深夜被人们的叫喊声和枪声吓醒,从窗户看去,外面火光连天。我跑出房门,哥哥却急急招手示意我躲起来,我藏到书架后面。 外面的喧嚣就在耳边清晰刺耳,却又像离我很远,很远…… 在世界渐渐安静时,我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 有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又从书架的最高处抽出一本书,我的心跳得很快,姿势几乎由蹲变为趴在地上。 书被人扔在地上,我心里咒骂着,但又感激这汉字的博大精深,让那粗鄙的外国兵不懂欣赏,才使我逃过一劫。 焦味进入我的鼻子,他们大概是想一把火烧掉这些他们眼中不值钱的文字,我看着火苗向上蹿起。 在哥哥教我读过的诗中,它们常被喻作强烈的希望或炽热的太阳,此时的我脑中却想不出任何修辞,只觉得自己将被这滔天火海淹没。 书房的窗子开在高处,此时却被人从外面撬开,一个青年人的头探进来四处张望,我问他呼救,也不知怎就认定了他是好人。 只喊了一两声,口鼻就呛进浓烟发不出声来,所幸他似乎听见了,进屋查看,在书架后间发现我后,把我扛到他背上,翻窗出去。 走出浓烟,我这才看清他的一身军装。 他的身子算不上多么强壮,大概因为看上去比我才大几岁的缘故,身子有些单薄。 却依旧在这样的环境中,给人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他带我穿过院子。在看见哥哥倒在血泊中的身体时,我收紧了手臂,勒到了他的脖子。 他短短停顿一秒,把我向上颠了颠,又坚定地迈开步向前走。 我咬着嘴唇,没有哭出声。 他带我回到他所在的军营。我认生,只跟他一个人走,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生怕被丢下。他与我哥哥一般高,不如我哥哥白净,脸上是硝烟弥漫过的英气。 行军至溪边时,正逢农历十五,圆圆的月亮映在溪里,波粼粼,流水不息,却带不走那月光。 我睡不着,他好像也是,连队连长难得让大家停下来休息,我们坐在溪边,我看月,问他:“你会想家吗?” 没人回应,我偏过头去看他,发现他正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 我重新抬头赏月,听见他说:“我没有家。” “我也没有家了。”我答。 “你至少有过。” 我们不说话了。 我有些担心,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在心里挑挑拣拣之后,也选不出别的我算得上了解的东西,只好开口他分享了几本我喜欢的书。 他不答话,只是应声,我见他如此没兴致,怕是自己分享太多,夺了他话头,便又问:“你呢,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书?” “这年代,我这条件哪里找得到书看。”他笑答。 我心里一凉,懊悔自己又没选中合适的话题。 “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挺有意思的,哪天这仗打赢了,有机会了,我一定去找来看看。” 他说的很认真想了想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读书挺好的。 他挠挠头,朝我腼腆地笑笑,月色下,他的轮廓褪去了些军人的硬朗,泛起了些柔和的光。 走在一起久了,连队的其他人就开起了我们的玩笑,有人让他积极冲整陷阵.仗打完了就能娶我回家还问要不要他们做见证,给我们俩定亲。 每次听到这话,他都只是低头笑笑,佯装不耐烦地挥手起他们走。 而我却总想起我堂姐出嫁时的样子,嫁入的是城里另一户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大家都道才子佳人。 出嫁那天,十里红妆,锣鼓喧天,我却只记得接亲现场,新郎官掀开新娘子头上的红盖头时,两人脸上都没有笑意。 我从此害怕婚姻,不想变成那金丝笼里的金丝雀。 他察觉了我每次被开玩笑时情绪的低落,让他的朋友们以后少说这种话。 有次他挖出了一个红薯,偷拿连长的打火石弄了堆火把它给烤了。 当他把一整个散发着香气的烤红薯举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你不要贿赂我,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他惊得手一抖,差点把那个战争年代无比宝贵的烤红薯给掉在了地上。 他开始笑,越笑我越气,跺了跺脚,转身跑了。他追上我,说:“行,不给你吃烤红薯就是了,你听我给你吹首歌总行了吧?” 吹首歌,吹什么歌?用什么吹?口哨?好奇使我停住脚步,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短短的竹笛,我见过陶笛,见过骨笛,却没有见过做工这么粗糙的竹笛,我看他能用这个吹出什么来。 当笛子放在他嘴边,真的流出了婉转的歌,旋律有些熟悉,我像是在哪听过却又叫不出名字来,音质不算好,但旋律依旧悠扬。 他吹完,我给他改掌:“吹得很棒,这歌叫什么名字?” 他脸上泛起红晕,在黝黑的皮肤下并不显眼,以至于我怀疑自己可能是看错了。 他说:“我忘了。” 经过几个月的行军,我们连成功和大部队汇合,司令官来慰问各连的时候看见我,问:“小姑娘,多大了?能干卫生员不?” 我不知所措,行军几个月偶尔也会帮连上卫生员打点下手,但这样的工作我是并没有多感兴趣的。他了解我。虽然为了战争需要我也是愿意的。 他替我说:“这孩子脑子不错,读书多,让她去当电报员吧,做点文字工作。” 谁是孩子?脑子不错管什么形容?我心有不满,却没有和平时一样同他斗嘴,因为他推荐的这个职位挺合我心意。 司令员点点头,把我带走去学摩斯密码。临走前,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他的眸子沉下去,半晌招头笑了一下:“好好听话,不许吃别人的烤红薯。” 语气依旧不正经,可我总觉得他的笑不似从前了。 电报员的工作我上手得很快,干了没几个月就被转去发密报,这段时间里,最开始常常会想起他,后来工作量日渐增多,白天夜晚连轴转,想起他的次数也就渐渐变少了。 直到我接到一项工作——发一份密报给第一军某连的一位连长,那是他所在的连队编号。 突然很想他。 想他那边最近战况如何,有没有受伤,子弹从耳边擦过的时候他会不会怕,想他会不会也有想起我,队友们会不会还开他的玩笑,而他又会不会真的把那些玩笑当真… 如果当真了呢,他会不会正在冲锋陷阵,要聚我回家?呵。 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在可笑,收了心,去打那份密报,可每敲出一个符号,我的心就沉一点,呼吸被堵在胸口。 我反复检查好几遍后才发送,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要扶着桌子借力,我挪到窗口,想透口气,那份电报的内容我至今仍记得— “请前往南部战区阵地支援第二军11连。” 离那份密报发出不久,就传来了南部战区阵地作为重要关口成功守住的捷报.参与本次战役的全体士兵记三等军功。 此时已至春日,译电员所驻扎的营地周围我叫不出名字的树种绿得春意盎然,我又想起他。 锃亮的军功章戴在那个生机勃发的少年身上一定颇为相配,如果战争结束后还能有机会,最好是我亲手为他戴上。 我这么想着,扬了扬嘴角,心情愉悦回位置继续工作。 在部队与我关系投机的一位战友走过来跟我说:“门口有人找。” 我走出去,一位身穿我所熟悉的军装的男人朝我敬个礼,我看到了男人胸前的部队编号,再次确认,是他所在的连队。 我有点期待,是他带了什么东西给我吗,又有点害怕,会是不好的消息吗? 我接过男人盖来的用蓝布包好的东西,不轻也不沉。 我当着男人的面打开。 一套染血的褪色的军装。 “他说他没有别的家人,如果他阵亡了,让我们把它带给你,”男人说“他在保卫阵地的战役中牺牲,记三等功。” 我的手在抖,血直往头上涌。 我那春光明媚的少年,破碎在春风里。 眼泪滴在旧军装上,我慌忙把蓝布盖好,向男人不成声地道谢。 那夜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又拿起那套军装,我把它抖开,一张纸条从口袋飘落,纸条的正面是一幅简单的素描。篇幅所限,细节并不生动,可我仍一眼认出。 那是我。 纸条的背面写着几个书名,那些我喜欢的,他说有机会是会去看看的书,最底端是8个用点阵表示的符号。 我愣住。 摩尔斯密码。 ILOVEYOU 我爱你 怕打扰大家睡觉,我不敢哭出声来,我只是拿起那件军装上衣,一遍遍吻着胸口处被血染红的布料,我没有擦眼泪,泪水浸湿衣服,将血变得鲜红。 鲜艳却不鲜活。 如果他真的喜欢我的话,我能回复的,也就只有“谢谢”二字了。 谢谢那天火海汤汤,你护我渡过一动。 此后我一直从事译电员的工作直至战争结束,又退伍回到百废待兴的家乡任村支书,我嫁给了一个来这里支援新城建设的外地青年。 青年有礼貌,踏实,有责任心,我们并不相爱,但也不会相约束,我们都会尊重对方。也都明白并接受婚姻不过是搭伙过个日子。 我们没有举办婚礼,而我也自然没体验盖着红盖头一身红衣,等着新郎掀开的那种心情。 不过这样也好,免得我的晚辈的旁观婚礼时看见新人都无笑意,也像年幼时的我一样对婚姻产生阴影。 哦,还有,我一直带着那套军装。 再过几年,我去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婚礼上两人都笑面盈盈,敬酒,对拜。 婚礼的结尾放了首歌,熟悉的音乐突然撩动了记忆深处的那根神经,这首歌的旋律有很大一部分与他曾吹给我听的重合。 我惊慌失措地问同桌的人:“这首歌叫什么?” “你没听过吗?《康定情歌》啊。” 听过,我听过。 在它尚未发行,还是一首四川民歌时,我便已听过了,我听过。 我曾一直以为我的放不下是因为那未报的救命之恩,如今才明白,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为他穿上红色的嫁衣。 我和他的年代,战火纷飞的枪炮声盖过悠长情歌,加密的电报里不许说一个“想”字,连最后的告别,我都未能见他一面。 可我现在所流的却是幸福的眼泪,只因我还留着那套褪色军装,辗转多条战线,无言的无奈的无数的挂念,近千个日夜的分别,他终于还是,回到我身边。 我替他领了那枚勋章,替他别在胸前,我的少年,仍在我的记忆中飞扬。 我想给他发一份加密的电报:谢谢那天火海汤汤,你护我渡过一劫。我爱你。 我想,他一定能破译的,即使远在天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jb/18557.html
- 上一篇文章: 为什么又买了一本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