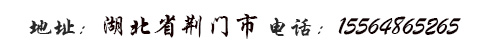岛屿与肉身
|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张爱玲诵读嘉宾 史玉娟 我叫史玉娟 热切的青春留在了北大和英伦的校园 如今工作和生活在上海 经历的世界越复杂 自我的判断就会越混乱 我无法给自己贴标签 越是缤纷迷乱 张爱玲倒越是明显 她是深海中的那座岛屿 她是旗袍下的那具肉身 史玉娟说这是迷茫的第四个年头,在这一年的下半段终于暂时结束了迷茫。 我叫史玉娟,年我到北大读研,那一年北京的秋带着缤纷的香味,在我记忆中悠久留长。人生的小目标实现了,以为从此便无忧无虑。那时的天空是真正的蓝,落叶是迷人的金黄,湖水是纯净的绿。 我用一点点功念书,用很多功做其他事。我触摸到世界精彩,就想要让自己丰富起来。相比较几年前硬着头皮做统计学习题集和神情泯然在天台弹筝的那个我,已不再感到周遭是寂静无人的孤独,亦没有要突出重围的决心。我感到幸福,被厚重的安全感包围着。 念着不急不缓的书,谈着不温不火的恋爱,在成功的喜悦和厚重的安全感之下,快乐却越来越淡。丰富固然体验到了,但缺乏一个重心,那个你认为重要,但不那么容易得到的东西。是下一个人生的目标。我花了很久,走到很远的异国他乡,度过一段忘却现实的日子,才终于在某一刻忽然明白下一站在哪。 落地的感觉是踏实的,尽管我的真心牵引我来到这座天空灰蒙的城市,但比起英国的璀璨华灯、瑞士的澄净湖水、荷兰的烂漫花海,德国的童话森林,它更让我确信存在的意义。这是年,结束迷茫的第一个年头。 此时我理解快乐是无法纯粹的,无忧无虑的世界也不一定给你真正的快乐。你必须体验复杂的情感,才会明白纯粹的意义。张爱玲对于我的意义,正是这种复杂之中的纯粹。在纷乱世事下,活在关系复杂、亲情支离破碎的大家庭,她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作为生活的旁观者,她缄默持重,却洞晓世事,将华美的袍子掀起,拈去一个个虱子。即便是被政治裹挟的爱情,她也能从中抽出温柔来,凭这一点暖,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所拥有的真性情和自始自终的纯粹,赋予她遗世独立的美和动人的意味深长。 我无法给自己贴标签,我经历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内心却越来越纯粹。我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看到听到触摸到花花世界,但想拥有的只是一点点,这样个人,任何标签都组成不了的人。如果真的需要,那就用一种颜色,它是我某天看到的一家店铺名,它一下击中我:naiveblue,天真蓝。 《异乡记》节选 张爱玲 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处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罢──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找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需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彷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腐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鎗,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彷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櫈,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彷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医院里未回。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枱抹凳。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斑斑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只有那么一个年青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彷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毕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拍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在电灯的照射下,更可以觉得那一房家具是女主人最心爱的──过了时的摩登立体家具,三合板,漆得蜡黄,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纸糊的,浆糊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点凸凹不平。衣櫉上的大穿衣镜亮的如同香烟听头上拆下来的洋铁皮,整个地像小孩子制的手工。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曲。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查点一过,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决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 — 选自《异乡记》 往期推荐 《一叶沧海济扁舟》我自己的张爱玲肆拾伍 诵读:蒋孝良 ▼ 申请诵读 永不过时的作家 一再重演的故事 这是你的舞台 请同我们分享 你与张爱玲的故事 我们的联系方式 邮箱: qq.如何防止白癜风复发太原白癜风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qingguo.com/lbzzc/12560.html
- 上一篇文章: 始于小爱,终于大爱,韩红的慈善如此感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