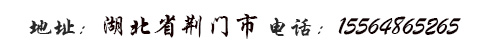作家天地bull原创金萍伸
|
白癜风专科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原创·散文 木舍手记(节选) 伸腿班金萍 我家屋后有个伸腿班在我四岁牙牙学语的时候,老家屋后有个伸腿班。什么叫伸腿班?就是在乡村小学之外,为了方便周围孩子入学,办起来的小小班。这个班有七八个人,也有十几个人的,读到二年级就转到正式的小学里去了。在家门口读小小班,非常方便。一个伸腿班就一个老师,老师都是多面手,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劳动都是一个人来。我家屋后的伸腿班,办在一个比较闲置的牛屋里。牛屋里有一头老牛,还飘散着很浓的牛的味道。有一天,平常没人去的牛屋里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歌声:“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歌声把我们这些乳牙未退的孩子都吸引过来了。平日里,家里大人都忙着下地干活,把幼小的孩子像泥蛋儿一样的顺手一丢,爱去哪玩去哪玩!收工回来,扯着嗓门喊一通,孩子就像小鸡似的,扑棱着翅膀朝家飞奔。可是,那天,我们一帮孩子都被牛屋里的歌声吸引了,全都趴在了牛屋的门口,一步也不愿离开。到了傍晚,牛屋里的孩子放学了,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拉手走出了牛屋。我们几个更小的孩子眼都看直了!牛屋里打扫得很干净,最前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小黑板,两边还贴着红红的对联。我们几个小孩子都趴在门边上不愿走开,那个笑眯眯的老师走过来轻轻地拉起我们说:小朋友,快起来,我们要放学了! 我们爬起来,站在门口,心里想:他的声音真好听! 那天晚上,是奶奶把我抱回家的,当时,我抓着牛屋的门鼻子,哭着喊着就是不愿意离开!奶奶尝试着拉开我的手,情急之中,我竟然在奶奶的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我躺在地上哭闹、打滚,谁说了也不算,我就是要上学!直到父亲母亲都跑来哄我才算了事。 为了能到牛屋里和别的孩子一样读书上学,我当夜发了烧,嘴唇上起满了燎泡。母亲说:等退烧再去上学吧!我又哭了!父亲说:你还小,不到入学年龄,要是你跟不上,就得立刻回家来跟奶奶一起玩两年再去!我点点头答应了。 在我的村庄里,孩子上学是大事,不比娶媳妇、盖房子动静小。母亲忙着给我缝新书包,奶奶忙着给我做新衣服,父亲忙着到集上去买铅笔、本子、铅笔盒。一大早,全家梳洗干净,奶奶、父亲、母亲带着我一起跪拜祖先、跪拜中堂,父亲告诉我,头上中堂上写的是“天地君亲师”,是一个孩子一生中首先要敬畏的!我虽然听不懂,但是能够看到大人的表情是严肃的。大人的话是不可违背的。父亲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也跟着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父亲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也跟着念。父亲让我对着中堂磕头,我就认真地磕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天做的一切,都是很神圣的。 家里跪拜完了之后,大人们又带我去了祖坟地。放了红红的鞭炮,奶奶和父亲又一一告诉我坟地里都长眠着我的哪些先祖,他们活着的时候,都做了哪些大事好事,有哪些了不起的地方,作为后人,该怎样继承他们的优点,修正他们的缺点和不足。比如说:我爷爷性格暴躁,重男轻女;我奶奶持家有方,刚毅睿智。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我的一门心思是,不管说什么我都仔细听着,只要让我上学读书就行!奶奶还教了我一支好听的歌:草叶青、草叶黄、我是小小读书郎;晨起读、灯下背、四书五经我都会;老师好、同学早、读书的孩子有礼貌! 这些都做完了,还没结束呢!还要喊来几个家门里的大一点的孩子们,在一起吃顿饭,饭前要拜灶老爷,宣誓要珍惜衣食饭粥、珍惜劳动汗水;饭后一起拜先生,向先生保证好好读书、好好做人。我记得,当时的“先生”就是父亲贴在门上的一幅画,画上是谁,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很消瘦,鼻直口方,正襟危坐,遥看远方,现在想想,应该是村里都尊重的一个有学问的人吧!因为我和大孩子们一起跪拜的时候,父亲、母亲和奶奶也都一齐跪下来了呢! 最后我和大孩子们一起手拉手转圆圈,做一种村庄里孩子常玩的叫“刮大风”的游戏,表示团结、勇敢、不怕困难。 当时村庄里的人家,孩子入学的时候,都要经过这样麻烦的程序。因为每家都对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通过这样认真严肃旳仪式,告诉孩子,从入学的那天起,你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有学问就该有担当,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上学的仪式终于在眼泪和欢笑中结束了,我的小小班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伸腿班的老师和孩子们其实,我的秉性早在幼儿时期就显现了出来。母亲说我小时候很犟,想要什么或干什么拼着命也要得逞,目的达不到就拼命地哭,顺地打滚闹个没完。四岁那年的哭闹,是我人生场景的第一次亮相。 我家老屋后面桃园旁的牛房里办了个校外伸腿班。一个留着光头、腰间系一根粗大的老蓝布腰带的民办老师,每天在牛屁股后面用赶牛鞭点着挂在墙上的木锹,教那些写在木锹上的“a、o、e”。那些“a、o、e”是用石灰粉写上去的,敲一下便有白色的粉屑掉下来。在家我也常看到母亲用那些石灰粉搓在脸额上,由别人用粗白线揪额角上的汗毛,村里人叫开脸,只有结婚过了门的小媳妇才去找人开脸,那脸一开,便不再是姑娘了。光头民办老师张大嘴巴声音洪亮地读着写在木锹上的拼音字母。牛铺上蹲着七八个“鼻涕虫”。虫儿们个个皆手背于后,胸挺于前,童声朗朗中听。母亲说,我总是没日没夜地倚着牛房门朝里探头,奶奶死活也拉不走。有一次阳春下起了桃花雪,飘飞的雪絮将我的小棉袄都打湿了,可是我依旧不肯离开牛房那扇椿木门。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滚在地上蹬着双脚,喊出了一句让母亲既吃惊又欢喜的话来。母亲说,要上学也得等到秋天新开学才行,半路上插班咋能跟得上呢?可是母亲经不住女儿的眼泪,就软着心把我交给了牛房里的那个光头民办老师。 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民办老师留着乌黑的两撇小胡子。只要一念书张口讲话,两撇小胡子就神气地上翘,给人一种精神升腾的感觉。民办老师一个人全包了伸腿班的全部课程。教完了语文算术,劲就松了大半,挥挥手让虫儿们三五成群去桃园里撒尿,自个儿就把大脚丫子翘在前排的泥凳上眯盹。撒丫子的虫儿们回来了,民办老师就讲故事,讲刘文学,讲张高谦,把虫儿们都讲得进入了角色,人人都觉得自己就是刘文学,就是张高谦。虫儿们听着听着,就闻到了一股异味。那是民办老师把手指伸进脚丫里来回抓挠了。民办老师还给虫儿们说,长大后千万别穿袜子,只要穿袜子,就会得这种痒死人的臭脚气病。 我那时极爱听民办老师讲故事,只要见他那两撇小胡子一上翘,我们这些虫儿全都来了神,多少年后,那些故事不但没有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反而愈发清晰了。特别是关于女人和鸭子们的故事。第一次听到两个女人千只鸭的故事的时候,一帮虫儿谁也没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笑的。只是民办老师讲完了故事顺便出了道算术题,意思很简单:两个女人等于一千只鸭子,那么问一个女人是多少只鸭子?我们当时还没有学除法,虫儿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回答出来。民办老师“唉”地叹了一口气,课也就下了。 讲过这个故事的第二天早晨,民办老师正给我们上汉语拼音中的韵母课。突然,一个男同学举手报告要发言。民办老师说:站起来讲!那同学悠晃着两挂拖至唇间的清流,底气挺足地说:报告老师,门口来了五百只鸭子!民办老师一吃惊,抬头朝门口看,却是他的盘了大髻的红脸媳妇立在门边上,是来向他讨钥匙的。民办老师立刻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抓挠着乌青的光头,最后竟笑出了眼泪。民办老师好久才止住了笑,走过去拍着那个男同学的大脑门说:我的儿,你的脑袋瓜好使,长大了准有出息!多年后,那个拖着两挂清流的男孩儿果真就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去了北京外贸部工作。偶尔一次重逢,共同谈起了五百只鸭子的典故,无不笑得泪光灿烂。我们那帮虫儿全都变成了鸟。而我们的那个乡间民办老师却因多年转正考试达不到分数线,贫病交加而最终变成了土。民办老师患的是肝病,先是黄后来还是黄,黄得发亮。民办老师是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先买点板蓝根喝了,不顶用,又去集上医疗室买了几包板蓝根大青茵陈喝了,还是不顶用。民办老师的工资从五元涨到八元,又涨到十五元三十五元,可是搁不住花,便去四乡寻那些有疗效先例的土方。土方终于在老师身上一次一次失效。民办老师眼睁睁看着自己不能再去牛房里敲着锹头念写在上边的“a、o、e”,终于绝望地丢下红脸媳妇,丢下一班“虫儿”,撒手西去了。民办老师死去的时候正是四月,万物生长的季节,激情勃发的季节。 民办老师的死讯飞得很快,民办老师的学生们,特别是那些混得人模狗样的老虫儿们,开了长长一串乌光贼亮的轿车去乡间坟地吊唁。 故乡的土地油绿明亮,一排排钻天杨正在道边悄悄生长。民办老师没有遗像,他的“五百只鸭子”红肿着双眼哭着说:老师活着的时候多少次说过,要去三十里外的镇上拍一张照片的。他还说,要不趁着还能看得过去拍一张照片,将来老了连张遗像都没给后代留下。老师还特别提到,拍了照片多洗几张,分别寄给那些乡旯旮里飞出去的“鸟儿”看一眼,要不然,长大的孩子就记不准他是啥模样了。可是,拍张照要跑几十里,他一个人包一个校外班,终于也没有抽出个空。师母的一番话,将诸位老虫儿们的眼睛全都弄湿了。十几架进口的国产的各种型号的相机一起按动快门,咔嚓咔嚓拍个不停。拍了故乡无边的麦田,高高的杨树,衰老的村庄,还有那个跪在地上拽也不起来的白发师娘。她已经全没了当年的壮实和风韵了,她说,老师走了,她也快走了。 我特地去看了当年为之向往哭闹的那个校外班牛房。那里的牛早已没有了,破房子也没有了。只留下一片小土房的废墟。零零落落,横七竖八的,偶尔露出大小不一规则不同的青砖痕迹的墙根。我将眼前的一切都拍了下来。我想,这一生我都会记着民办老师的模样。他一举手一投足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三十多年前,就是他中气十足地扬着嗓门大声说:大丫,你的“a、o、e”读得好极了,比早来的孩子读得还好!就在民办老师眉毛颤动胡子也跟着颤动的夸赞声里,我的书读得愈发见长进,变得就像四月里高天的云雀,响亮而又中听。民办老师课余爱扭秧歌。他粗壮的腰里那根细细长长、通红如火的红绸点燃了我日后生命里永不熄灭的激情。于是,四月的艳阳天里,我虔诚地跪在掩埋了民办老师的黄土地上,咚咚咚!坚定不移地磕了三个响头。于是,三只硕大的“鹅蛋”便突兀地在我眼前终日晃动,如警示一般。 图文来源:本站原创,全文发表于年第7期《作家天地》;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如有不便,请联系删除。 投稿邮箱: 小说:yszx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zc/14078.html
- 上一篇文章: 迟子建花瓣饭
- 下一篇文章: 草木诗心左边右边22周年暨第三届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