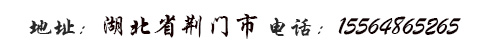青莲露从今夜白
|
福州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5218805.html露从今夜白董方军矩形色块 气温骤降,整个天地雾蒙蒙的,混沌一片。月亮白晳的脸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黄河故道两侧一望无际的森林、广袤的田野、星星点点的村庄都显得朦朦胧胧,恍若仙境。奶奶带着我从菱角街匆匆赶到渡口,正好赶上最后一班渡船。空寂的渡船上、泥泞的小路上、小前庄的菜地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霜。我们走过时,留下一串我小小的脚印。天越来越暗,奶奶帮我点亮手中的小灯笼,我隐约能看到芦苇叶、山芋叶、槐树叶上滚动着一滴滴小小的、圆圆的、亮亮的露珠。 我穿过小前庄,路过前庄东南方向的汪塘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朵非常妖艳的白莲花,便指给奶奶看,往身后看时,奶奶忽然不见了。奶奶住在前庄大爷(伯父,安东方言)家,难道她先回去了?我到大爷家的锅屋、堂屋找了个遍,却没有发现奶奶的踪影。最后在院子后墙根发现了一排精致圆润的骨头,我朦胧中意识到:奶奶被大爷家人烀(煮)吃掉了。这样一想,我蓦然惊觉,我人生的记忆从此开始。我飞跑回后庄家中向母亲报告。母亲叹息说:“难怪小四子老往前庄跑,原来是找奶奶呢。” 据母亲说,奶奶长得矮小瘦弱,常年躬着腰,头发稀少,但慈眉善目。奶奶特宠我,只要我到前庄大爷家去,奶奶就笑得合不拢嘴:“大四子来了,快给奶奶抱抱。”拿饼干、糖果给我吃。可惜我对奶奶一点印象都没有。妈妈说:“奶奶是你虚3岁时没了的,你4岁才开始记事,哪能记得?” 奶奶听觉过人。那时我还没出生,我们家还和大爷家住一块儿,西侧一间小草屋里。一次,奶奶忽然听到小屋发出轻微的吱吱声,直觉让奶奶飞奔到屋里,抱起正在熟睡的三哥,刚到门外,房梁就塌了,床被砸得断成两半。想想都后怕,都说三哥拣了一条命。 小屋不能住了,好在爹爹(涟水方言:祖父)是远近闻名的木匠,找了一帮人,就在后庄搭起了草房。石头做根脚,用烂泥砌墙,顶上苫上茅草。房子不大,用篱笆隔成两间,里间为父母住,外间为锅屋,也放了一张床,大哥二哥三哥挤在一张床上。这样的房子是经不起岁月的侵蚀的,墙的西南角渐渐有了裂缝,只得刨了一棵大槐树,砍掉枝叶,用树干加固支撑。而房顶的茅草在与暴风雨的抗衡中尽管勇敢呼号,却也渐渐落了下风。外面大下,屋内小下。母亲把大大小小的洗脸盆、洗脚盆找出来放在漏雨的地方。一家人就在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中入睡。而父亲不敢入睡,半躺在床上,一面抽着自己用烟叶裹的旱烟,一面以奶奶遗传给他的敏锐的听觉,听着房梁的动静。母亲说,父亲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抽烟的,一支接着一支,熬过漫漫长夜。所幸房子虽风雨飘摇,却一直没有倒下。 大姐和我就在这屋子相继出生。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挨批斗。母亲不放心,就叫大哥去看看。大哥那年15岁,第一次出远门,他到了三十里外的安吉小学,看到院墙上贴满大字报,父亲被画成蛇和牛。身为校长的父亲,正被红卫兵小将们毒打。父亲手肿得老高,吃饭时,连碗都端不起来,还得给造反派送饭。大哥是个急性子,当时就操起一根木柴,要跟人家拼命,被父亲严厉喝止:“住手!你一米八几的个子,出手重,这一棒下去,他们不死,也得残废!他们和你一样,也是小鬏(孩子),懂得什么?我没事,快给我回家去!” 据说,我3岁那年,父亲回来了,根本不认识我这个儿子,大约他被折磨得够呛,也许面目有些狰狞,我吓得哭了起来。 尽管一家人蜗居在不到30平方的小茅屋里,尽管父亲在外面无端地受了不少罪,但他相信党,照样乐观向上。春节时,铺开红纸,挥毫泼墨,门上春联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中堂对联为:“一家七口,耕读两行。”不久,他就恢复工作,他还在原来安吉小学的基础上,建起了全县第一所民办中学。安吉中学的兴办,解决了余集公社周边的无数农家子弟上学难的问题。我后来工作中遇到很多人,既有各行各业人才,也有村委会主任、县长,提到我父亲都肃然起敬,主动跟我说:“我是你爸学生。”甚至还有在蒙古工作的学生一直认我父亲为爸爸,还寄了张整羊皮过来,我父亲一直舍不得穿,在母亲的劝说下,才用它做了大衣。 当然这些苦难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那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整天用粪勺(小型铁锨,平时挖泥、挖塘、铲草、铲粮食,只有上冻天拾粪时才用来铲冻起来的狗屎、牛粪。这个粪勺当然是从没用过的,是干净的,是我的专属玩具)作为想象中的老黄牛,扣上一根绳子,左手扶犁,右手牵牛,早上一睁眼就到屋前空地上、庄前小路上推着奔跑(耕田),一直到晚上,口中“哞哞”不停,天天如此,乐此不疲。 我觉得做一个放牛郎,做一个在黄土地上耕田驾车的农民,是我最大的理想和快乐。我看到在蔚蓝的天空下,堂哥小鲁班(他的木匠手艺得爹爹、大爷真传)坐在高高的牛车的麦秸垛上,仿佛坐在云端上,把鞭子甩得叭叭地响,高声吆喝着高大威猛的黄牛,恍若天人,那是何等的威风。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崇拜的偶像。 母亲看我玩得开心,当然也很高兴,我自娱自乐挺好,省得动不动要抱,还不时要吃奶。母亲要到生产队干活,回家还要煮饭,刷锅,喂猪,她有做不完的家务。 可是到了大年三十(除夕),我还在推着粪勺满院子跑,母亲就有点担心,我听到她小声对父亲说:“小四子大年初一会不会也这样?”到了晚上,母亲左叮咛右嘱咐:“明天是大年初一,不要推粪勺子,记住了吗?”我挺纳闷:为啥大年初一就不能放牛呢?第二天早晨醒来,正准备像往常一样闭上眼睛“哞哞”几声起床,忽然想起母亲的告诫,赶紧闭上嘴。睁开眼睛,意外发现枕头边有一个油纸包,里面有二十多粒金黄色的油炸果子,香喷喷的;几片白玉似的大糕,透着一股甜味。我心中狂喜,美美地吃起来,接着起床,吃汤圆,然后和古小四、田小四、余小四等几个小伙伴们一起打梭子、滚铁环,放牛这事早忘到九霄云外了。也就春节那几天大鱼大肉地吃得过瘾。元宵节过后,又恢复到了半饥不饱的平常日子。尤其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没有粮食吃。一家七口,父亲在外教书,三个哥哥上学,姐姐和我还小,只有我母亲在生产队苦工分,妇女属于半劳力。到分粮食的时候,我们家不但分不到一粒粮食,还得倒过来挺(付)出一点粮食给人家强劳力。母亲从生产队里负(借、赊)一点玉米,又拿着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到菱角街上换点荞麦。安吉中学的学生家长到我家来玩,没想到我家那么穷,连隔夜粮都没有,回去后,就拖了一口袋山芋干来,有了好心家长的接济,我们才勉强度日。早晨棒面(玉米面)稀饭,中午棒面稀饭,晚上棒面稀饭。日日如此。说是稀饭,照见人影。其实就是一点点棒面加一大锅水。吃过早饭,一会儿就饿了。没有咸菜,父亲就用一只碗,单独装一下子稀饭,放几粒盐,放在桌子中间,权当就饭的咸菜。我们喝一口自己的粥,再用勺子舀一口饭桌中心的咸粥。大哥在余集中学读高中住校,我们家交的粮食只够大哥吃五天的,另外两天他就靠喝水度日。大哥饿啊!大哥天天盼着回家,到家就可以喝到粥了。他最多喝过八碗。他在家中要挑水、推车,干重体力活。二哥喝了两碗,也想再喝。母亲有点着急,都这样喝,过不了几天就得断顿(没饭吃。当地民谣:城里小孩怕地震,农村小孩怕断顿,机关干部怕癌症)。就阻止道:“小二子,你没你大哥商务(方言:活计)重,你不能像他那样吃。”二哥虽憨,但脾气倔,不服气地嘟哝道:“割草拾粪就不是商务啦?”赌气放了碗,背起箩筐拿着镰刀挑猪菜去了。从此只吃两碗,绝不多吃。 三哥一看,父母是指望不上了,只能自救了。把锅里蒸的小的和虽然大却有点发黑的山芋(主要是喂猪,好的山芋早就吃光了),夹了两个大的,捣碎,狠狠地倒了小半碗花生油,搅拌一通,饱餐了一顿,抹了抹油嘴,上学去了。 大姐看我饿急了,把花生饼子取出来,那是生产队榨花生油之后的花生渣子,坚硬如铁。姐姐力气小,斧头只能削出一点点饼屑,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咀嚼,减轻一点饥饿感。 有人说你不能对着花生饼子啃吗,不是不想,是真的啃不动。如果能啃动,早就被几个哥哥啃光了。他们也只能用斧头或刨刀削下一点屑子。有点像望梅止渴,也有点像画饼充饥。但梅子和画饼毕竟是空的,这花生饼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但满足了精神上的巨大饥饿,也能实实在在地到嘴到肚,虽然也只能满足一点点物质获得感。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锅里往往只剩下锅脚(一丁点稀饭),兑点开水,盛到碗里,慢慢地吃。其实母亲是最饿的,但她总是说:“我不饿”“我吃不吃无所谓”。母亲和大哥常会饿得发晕,天旋地转。却不说自己是饿的,说是低血糖。此时,他们要吃一块水果糖或喝口糖茶才能缓过劲来。母亲自己忍饥挨饿,却千方百计让我们尽可能有吃的。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就挖蚂蚁菜、荠菜等野菜给我们充饥。有一阵还向饲养员讨点喂牲口的薄脆(豆粕),好像口感还不错。最难忘的是母亲用花生油炒榆树叶,用槐树花包馒头(我们老家把有馅体积大的包子叫馒头,无馅的实心的呈长方体叫小卷子),那是人间最好的美味。 我们这地方那时候是真穷,一年到头都是棒面粥,山芋和山芋干是主要干粮,只有来亲戚和逢年过节能吃到小麦面。清明节和七月半是鬼节,吃水饭(水饺,豆腐馅);八月半是团圆节,吃馒头和月饼;白米饭和猪肉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我们大队地势高,旱地,不能种水稻)。而我吃一碗山芋干,能剔出半碗山干头,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是坏的,苦,不好吃。很快就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了。 一天夜里,我正睡得沉。母亲忽地把我叫醒。我一看,母亲手中端着香喷喷的白米饭,粒粒如珍珠。我惊讶:哪来的大米饭。母亲说:“今天队里供饭。我跑回来的。快吃,我还要把碗还回去。”我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转眼就吃了个精光。母亲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后来才知道,母亲竟然一口也没舍得吃,那是“双抢”(抢收抢种)最忙的时令,母亲劳累挣得的活命饭,却只匆忙喝了口山芋干粥就又回队里干活。 那年大舅娶亲,中午的宴席开得有点迟。大舅最疼我,问我饿不饿,我点点头。大舅不由分说,就盛了大半碗红烧肉,我哪里知道轻重,全吃光了。长期没吃荤的小孩子,是个素肠子,又是虚6岁,一下子吃这么多肥肉,还没有吃米饭和其他素菜掺和,撞大发了。头昏得厉害,大人们把我扶到客厅小凉床上睡下,盖上被子。到傍晚的时候,我心中发慌,翻江倒海,狂吐一通。此时鞭声大作,大舅和大舅妈挤进门,一群人在后面起哄。我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地面清理干净,正准备将破盆里的秽物倒进废汽油桶里,但大舅妈已然将目光扫过来,显然来不及了,只得退后一步,藏到身后,微笑点头。幸而大舅妈没有发现,又将目光又移向了舅奶(外婆)。 为了缓解尴尬,也为了转移视线,我赶紧将母亲平时教的儿歌和来之前教我的喜话组合成一首童谣,半是自嘲半是对着新人祝福的唱道: 拐磨拐,请舅奶。舅奶不在家,就找大舅妈。大舅妈,没进门,大舅好心疼。看着外甥瘦,给了一碗红烧肉。外甥吃光光,吃完心发慌。又发困,又头疼,原来肥肉也醉人。舅妈舅妈不作声,生个儿子胖墩墩。舅妈舅妈快进房,马上生个状元郎。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舅妈也露出笑容。趁这功夫母亲早把破盆里的东西倒进废汽油桶里,并踢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新人进了洞房,众人又让我去摸马桶、戳窗户,也说了一阵喜话。众人又喧闹了一阵,才一一离开。我两腿发虚,赶紧回到小床上,又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恢复元气,赶紧拉着母亲的手回家。 麦子收下来后,我们最困难的日子也就过去了。夏天瓜架上爬满绿色的藤蔓,肥大的绿叶遮蔽炎炎烈日,留下大面积的浓荫。我喜欢坐在小竹凳上,观赏一个个艺术品一样的葫芦、瓠子,轻抚胳膊粗的吊瓜、番瓜(分别是架子上和地上的南瓜),指点大腿粗的冬瓜、柔软细长的丝瓜、短小精悍的小瓜(一种光皮的黄瓜)。我喜欢看着母亲挎着竹篮,采摘豆角(梅豆角、长豆角、蛇豆角)、茶豆角(扁豆角),和姐姐一起摘红大椒、紫茄子,听父亲讲“瓜菜代”的由来。这个季节我们有足够的瓜果蔬菜吃,能填饱肚皮。 秋天主粮吃的还是棒面粥,玉米收下来后,棒面饼也吃得多了起来。偶尔也吃几次小麦糊糊粥,最奢侈的就是锅底煮鲢鱼(三哥不知从哪里找的雷管,放在空酒瓶里,扔到汪塘里炸的鱼),锅帮上面贴一圈水踏饼(小麦面饼,后来就发展为著名的小鱼锅贴),水踏饼沾鱼汤,那是真好吃呀。 冬天吃山芋粥、山芋叶粥,各种菜粥,尤其是胡萝卜粥最受欢迎。当地有童谣云:“拖拉机突突突,小胡萝卜插菜粥。”腊八节吃腊八粥,母亲放花生米、黄豆、梅干菜等八样菜,放点花生油、食盐,吃得又饱又暖和,远比城里的八宝饭好吃。后来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到城里的渐渐多了,常常想起小时候的味道,有人就专门开粥店,比较出名的有海妹稀饭村、漂母粥店等。还有一家开在香格里拉的酒店——“安东之家”更厉害,把安东的各种美食挖掘出来,大大满足了安东人的重温童年生活的那种感觉。 但小时候想要吃上真正意义上的荤菜大餐,还得等过年。所以小时候都巴过年。三十晚上炸坨子(肉团子、肉圆子、肉丸子),母亲总是先炸素坨子,我们都等在锅边,眼巴巴地看着。豆腐坨子、萝卜坨子、山药坨子这些素的把我们的肚子填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才开始炸肉坨子。否则那点肉糊炸的坨子,根本不够我们这群饿鬼塞牙缝的。家家户户从腊月二十就开始忙年,做豆腐、百页(千张)、粉条,腌萝卜干子(安东特产,据说曾经是贡品,是宫廷必备的开胃小菜。另有歇后语叫安东萝卜干——刀刀见皮),腌雪里蕻,腌咸鱼、咸肉。大年三十中午是正餐,小米做的米饭,比现在大米做的还香。鸡鱼肉蛋八碗八碟,我比较爱吃的有高沟捆蹄、叽溜狗子(知了脱壳前挖出来洗净油炸)、黄花肉、杂烩(里面有安东鸡糕、皮肚、鱼圆等)、山芋粉块。 三十晚上吃孬的,这是母亲的主张,过年大鱼大肉太荤了,要寡寡(刮刮油)。喝山芋片茶或山芋丁茶,甜习习的,解渴,去油腥。我们这边说是喝茶,其实只是白开水,并无茶叶。放点白糖,叫糖茶;放点馓子,叫馓茶。将山芋切成丁,放在水里煮叫山芋丁茶。一家之主有时吃小锅饭,也叫早茶,开水里放点小卷子,打两个荷包蛋。这是父亲的专利,连我这个最小的最受宠的也不能沾光。早茶晚水的说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据说我们的祖上是从苏州阊门逃难到苏北这边的,想必是江南的习俗。 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这里吃汤圆,不吃水饭(饺子)。汤圆,很小,实心,其实不怎么好吃,中间放一盘白糖,沾着吃,才好吃。而我不太爱吃甜食,所以吃得很少。大嫂嫁过来后,见我不爱吃,就进行了改良,包了像小馒头大的汤圆,馅子是雪菜豆腐,由于糯米面不如小麦面紧实,馅子很容易漏出来,包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大嫂以足够的耐心包了一锅。那汤圆我是吃得最多也是最好吃的一次。 可是小时候的时间过得真慢呀,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供我们挥霍,好像永远用不完,大年三十总是姗姗来迟,我们总是等得望眼欲穿。 每天,母亲把门锁好后,就到生产队劳动去了。姐姐和我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门。姐姐和我呆呆地看着蓝天上变化的白云。有时像一团棉花、有时像一只白马、有时像老寿星,有时什么也不像。一看就是一整天。实在太无聊了,姐姐会帮我扎小辫子,因为头发短,只能扎朝天辫,而且皮筋不太好扎,姐姐就拼命地攥紧头发,其实是有点疼的,但还能忍受得住。那时老鼠猖獗,常常大白天就出来找吃的。一听到老鼠的吱吱叫声,我们就吓得到猪圈那边去。因为母亲交代:“好好看门,不准乱跑,不准到河边,不准爬树。”我们哪也不敢去,整天坐着发呆,那时的一年真长呀。可是猪也饿坏了,那天就从猪圈里跳了出来,而且很快不见了踪影。姐姐让我坐在原地别动,她去找大人,幸好爹爹在前庄。爹爹把猪找到,并驱赶进猪圈。我们才松了口气。 我每天也依然玩着放牛的游戏。 家里请人支锅。来了很多人帮忙。我来到东山头(房子东面),发现靠墙放着父亲出远门骑的永久自行车。咦,这车龙头,多像水牛的两只角呀。我马上找来麻绳,让三哥帮我扣到右边的牛角(手柄)上。三哥不理我,我只好自己踮起脚尖,将牛角系住,嗨!牵这牛可比推粪勺真实多了。马上开始,一拽牛绳,“哞”一声还没出口,龙头一歪,自行车失去平衡,重重地向我砸来。我顿时失去知觉,人事不省。据说那天三哥被狠揍了一顿。父母亲顾不得支锅一帮人,抱起我就往三里外的七堡跑,那儿的保健室有一名医叫木四先生。木四先生用听诊器听我心脏的时候,我朦胧地听到他与父母交谈。想睁开眼却睁不开来。又失去了知觉。然后在返回的路上,路过八堡的时候,我听到了两声庄子上的遥远的狗叫声,我睁开眼,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说:“有狗咬。”妈妈惊喜若狂:“醒了!”父亲也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小时候不知道怕,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黑不怕夜。天天在外疯玩,晚上也不想回去。不知是哪个好事者,吓唬前庄余会计家的千金小鱼儿,小鱼儿上哪去,都说“怕!怕!”,就缠着我,到哪儿都让我陪着她。我奇怪:“有什么怕的?”她左右看了看,小声地告诉了我,说是世上有一种东西叫马奇嘎,专吃小朋友,只在夜间出现,一般在外面,但有时也会溜到人家的床下,等小朋友睡着了,再爬出来吃。我望望浓得深不可测的夜色,不禁头皮发麻。赶紧借着微弱的星光,各自回家。吓得我从此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望望床肚底下有没有藏着可怕的怪物,可我们家的床是有踏板的,床的外侧用一块完整的护板与踏板无缝对接连成一体,根本看不到床底下,好在仗着有大人同睡,也就不想那么多了。可是一个人就不敢睡了。 笛子“呜呜”地响起来。一听到这悦耳的音乐,小伙伴们就兴奋起来,因为卖糖的来了。各自从家中跑出来。等我跑到村口的时候,小伙伴们已经围了一圈。卖糖的是个四五十岁的老头,个头不高,上身穿着漏着棉花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打满补丁的旧棉裤,头上戴着灰色三块瓦帽子,两个帽耳朵把脸紧紧包裹在里面,帽带系在下巴处。口中哈出团团白气。不知姓氏,也不知何方人氏,人们都叫他“三鼠吊子”。三鼠吊子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户,方圆百里没有不认识的。他的担子一前一后都是特大的箩筐,前面箩筐上面放着一个长方体木盒,上面盖子是玻璃的,盒子分成一个个方格子,里面是日用百货,针头线脑、水果糖、麻花、雪花膏、小圆镜子什么的。后面挑的是个长方体的竹篾筛子,里面有一块菜板,菜板上放着麦芽糖。我敏锐地感觉到箩筐里好像藏着一个小朋友。 小伙伴们围着货郎担子叽叽喳喳说笑一通,看的多买的少,说是买,实际上是用牙膏皮、破铁锹、坏铜锁、山芋换,我们都买了电光子(玩具子弹),放在玩具手枪上(我有一个木头做的手枪,中间用电钻钻了一个孔,食指正好可以放在里面,与真枪神似),一扣扳机,就“叭”地一声。这次三鼠吊子又有新玩意,他拿出一叠小画片,唱道: 马奇嘎,大肚脐,揣怀里,能避邪。狐大仙,嘴雪(很)尖,请家中,有姻缘。黄金浪(黄鼠狼),笼里放,狗不咬,鸡不慌。猪八戒,好吃鬼。吃一嘴,落(赚)一嘴。 我拿了一个大山芋,三鼠吊子笑着说:“只能买到其中一张哦。”我指着那个最精美的小画片:“就它了。”三鼠吊子说:“你真有眼光,这是马奇嘎。百怪之首。” 忽然传来一声极其细微的口哨。我立即听出这似乎是专门对着我的。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那小男孩,我感觉到他向我摇头,摆手。我背对着他点点头,还是交了山芋,从三鼠吊子手中把画片接过来。我从没见过世上居然还有这么精致的画片。一个身材修长的人,肤白唇红,似笑非笑。头戴红线帽,帽子顶部有一个小绒毛球,有点萌态可掬。上身穿着紧身衣,系红、蓝、黄、黑四色布拼接而成,分别绣着红心、黑桃、梅花、方块图案,上有围脖,下有裙摆。腰间还系了一条白丝带。下身穿着秋裤,左蓝右黄,脚上是高筒红靴,鞋头尖尖的,也缀着绒毛球。左手叉腰,右手拎着一个倒立的戴着小红帽的小人头,没有丝毫恐怖,反而有种顽皮搞怪之趣,只因小人头是此人的微缩版。画面线条如端午节扣在手腕和脚脖子上的五彩丝线,整个人物衣着华丽绚烂,发着炫目的光。我感觉一道美丽的光深深照进我黑暗的灵魂。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奇嘎?一点也不吓人嘛,而且好可爱啊! 人们纷纷聚拢来,三鼠吊子把后面装麦芽糖的筛子挪开,露出一个小光头,眼睛清亮亮的。“快把帽子戴上,别冻了。”三鼠吊子把头上的三块瓦扔过去,露出花白的头发。小光头又把三块瓦扔了回去,指着我说:“不用,我跟他借。”他对众人道:“我能把他画片上的衣服帽子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你们相信吗?”“不相信!”众人纷纷摇头。他说:“我是白素贞的儿子,母亲被压在西湖的一个塔下,我要去救她。可是没有盘缠。如果我能办到,请各位大爷各位大婶发发善心,凑点路费好吗?”众人都认为他说的是疯话,齐声答应:“好!只见他一晃身形,已稳稳地站到了筐沿上。众人都异口同声地喝了一声彩:“好!”天哪!他居然是光着身子的。虽然十岁之前我们都是光着身子的,但那是夏天。现在可是数九冬寒天,不穿上棉衣怎么受得了。我赶紧说:“你要穿画片上的衣服,拿去好了。说什么借字。”“那我就不客气了。”小光头伸手朝空中一抓,我眼睛一眨,他手中已经无端地出现一顶线织小红帽。他双手把帽下沿捏住,用力套在头上,帽顶上的小绒线球欢快地跳跃着:“我是马奇嘎!嘻嘻!”他朝我吐了吐舌头。咦?画片上的帽子不见了。他故伎重演,上衣、裤子、鞋子等小画片上的衣服居然全到了他手里,他很快穿戴整齐。众人再看小画片上的马奇嘎,居然寸缕全无,一丝不挂。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好!”众人纷纷慷慨解囊,有送钱的,有给米给面的,有给山芋、花生的。不一会两个箩筐就全装满了。我看着手中的画片,不禁有点遗憾:“画片失色不少。”不过想想帮助了小光头,也就释然了。小光头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安慰我:“放心吧。我临走时,衣服会全还给你的,你的画片会斑斓如初。” 我和小光头成了好朋友,他跟我讲了许多外面的故事。特别是讲他是西湖人,西湖如何如何美丽,夏天的荷花如何娇艳,莲蓬如何鲜嫩,莲子如何采摘。还讲了鸡头菱角。令我十分神往。他讲三鼠吊子是他的父亲叫许仙,但他没见过母亲:“她是个蛇精,被一个叫法海的和尚捉走了。为了躲避法海的追杀,父亲就将我剃了个光头,藏在货郎担里,逃到了你们这里。但我不能永远藏着,我要去救我的妈妈。” 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我们这边也有坏孩子,七步蛇就不客气地欺过身来,将小光头的帽子抢走,还戏谑道: 小光头,二斤半。卖给人家做瓦罐。瓦罐一只眼,真话假话全说反。 小光头可不是好惹的,拾起一块砖头,就追。吓得七步蛇扔下帽子,拔腿就跑。小光头一直追到小鱼儿家前面桑树林,找不到了才罢休。 小光头要离开了,我把小光头请到家里。抓了一把米,扔到铁锅里,但是我不会做,家里人就笑。母亲下了一碗筒儿面,打了一个鸡蛋。还吩咐大哥用独轮车送他们一程,三鼠吊子千恩万谢。小光头吃得一头汗,深深地向我母亲鞠了一躬。 月亮升起来,把满地的寒霜照得如同白昼。大哥将货郎担子里的货一半放到车上,推着车在前面开路,轧出深深的辙痕。三鼠吊子挑着担子紧紧相随。我和小光头走在最后。从后庄,到前庄,再从小前庄到古黄河边,洒满白霜的小路上留下我们深深浅浅的脚印。正好赶上最后一班渡船。空寂的渡船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银霜,芦苇叶上滚动着一滴滴晶莹剔透、圆润精致的露珠。三鼠吊子挑着担子上了渡船,小光头也一跃而上。船很快过了河,小光头向我挥挥手,他们消失在对岸的密林中。雾愈来愈浓,黄河故道两侧郁郁葱葱的森林、无边无垠的田野、万家灯火的村庄在朦胧的月色下越发显得光怪陆离、神秘莫测。整个宇宙云笼雾罩,扑朔迷离,一片混沌。 (作者系清江浦区人大常委会四级调研员) END排版:梁宵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zc/15192.html
- 上一篇文章: 这70种野货,吃过30种才算神仙
- 下一篇文章: 上海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品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