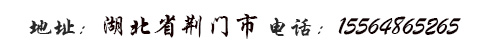灵异茶馆里的灵异故事
|
茶馆里的灵异故事 作者:乔北 畢業之後,整个北京都容不下我。几乎要到了喝毒自尽的时候,许欢江打过电话来,要拉我和回去開茶館。 听到这个建议,我本来是拒绝的。我又没有本钱,怎么开茶馆。可是许欢江说,你过来写写字,弹弹古琴,吹吹牛皮就好了。许欢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虽然整天没个正形,但办事还算靠谱。忽然从他那掉下来个没本的买卖,再加上我在北京已经有上顿没下顿的,所以我一拍屁股就回去了。 到了山西,发现许欢江这家伙连开茶馆的地方都没找到。我也没管,躺在家里很是腐败了几天,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早晨,他打来电话说找到一处旧院子,正合适。我迷迷糊糊地在床上接到这个电话,起来收拾收拾就赶过去了。 到了时,许欢江已经到了,这家伙收拾得人摸狗样的,站在一个古式大拱门前面青石台阶上,阳光照耀着,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笑吟吟地问我,来啦。 我点点头。初生的太阳照耀着,空气里还有露水的味道,很好的天气。 这是一處很舊的,似乎廢棄了很多年的晉商大院。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在明樓的正脊上盛開著。這當然是說磚雕了。花的旁邊還懸掛著大串大串飽滿的葡萄。整体感觉雍容华贵。院子是兩進,中間用一道九踩斗拱的中門隔開,北院都是高聳陡峭的瓦房,南院是鋪滿方磚的平房。院子里都没有裸露的泥土,外院用条石铺着,里院是方砖铺地。走进去满是尘土,院子里的地砖有的破碎了,裂缝里嵌着尘土,有些凸出来一点的,却光洁如镜,像常常有人走似的。砖缝里长出一簇簇的青草,窗棂干枯残破,看样子破败很久。 在門房的頂上,也就是大門上,悬挂著一塊不大不小的噴繪廣告牌,舊舊的,上面喷绘着一个留着秀发的女人。但头发太浓密了,看起來就是一團漆黑濃密的長髮盤繞在上面,只露出半张脸,年深日久褪色了,看不清五官,主要能辨认的就是一角惨白的下颌。这應該是塊美髮沙龍的廣告。房東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一直跟着我和许欢江转悠。看到我看那块广告牌,就探过脑袋来解释,說這是上一個房客留下來的,他只租了門房一帶,做理髮店。後來生意不好,就不做了。房東說这块牌子我們可以任意處理,他也早就想丟掉了。索性扔掉好了。 其他的改造麼,只要不損害房屋的原有結構、木雕和磚雕,也隨便我們怎麼搞。 房东說完就閃身了。临走还说,听说啊,这处大宅院的主人,原先就是个茶商。在旧茶庄里开茶馆,你们的茶馆生意一定会很好。 我们于是寒暄谦虚几句,打几句哈哈,送走了他。我比较奇怪,怎么连价钱都没有谈呢。我于是拉住许欢江问,许欢江说,这个房东是他爸爸年轻时候的朋友,偶然地一次脑袋抽风买了这处院子,但也没想到做什么好,一直荒废着。听说许父说他儿子要开茶馆,就主动提出来要把这处院子借给许欢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没提租金这回事。 我说这不太好吧。许欢江摆了摆手,把烟蒂弹开老远,说,这家伙还求着我家老爷子呢,随他去,不要白不要。 我其实并不是担心这个人情问题,总觉得这么优质的房产不要租金,怪怪的。但最后终究没有说出口。 大家其实都很開心,仔細制定了裝修計畫。我们計畫先粉刷,後裝潢,把院子好好整一整,爭取讓客人來了第一眼就喜歡上這裏。粉刷嘛,就是要把原來的牆皮鏟掉,然後用沙灰、白灰把牆抹一遍,然後再用滑石粉做鏡面拋光。木工呢,我們準備做槅扇,做博古架,還訂購了很多仿古家具,比如太師椅啊八仙桌啊,木料都是好木料,下了很大本錢,準備大幹一場。 许欢江还是那副德行,一说到要干活,要监工,立刻就跑没影儿了。没办法,只好我来干。其实我也知道,我不花一份本钱就能当合伙人,其实也就是过来给许欢江干这些杂活的,上来上去最后还是当了许欢江的手下,唉,也许这究竟是人生,没办法。 我于是请工人,找了泥瓦匠和木匠。这么多人驻扎在一起,我一个人还忙不过来,就让父亲母亲闲了的时候也过来。这院子空屋很多,我们就把里院的正房打扫出来,住在里面。 但是很奇怪,粉刷的時候灰泥抹不上去,试了各种办法,包括在灰泥里兑贴瓷砖用的胶水,还是不行。所有人多说这是怪事,可怎么办的。后来,还是有个工人出主意,用手握砂轮把所有墙壁都打磨一遍,磨平,然后用浆糊和黄草纸裱一遍。有些地方呢,我就诗兴大发,蘸墨写了很多狂草大字。有临自叙帖,有千字文,还有琵琶行。因为我非常感怀于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明月江水寒。当然这是后话了。 工人们本来是住在外院的南屋和门房里的。他们也很乐意,解决了住的问题,而且又离工作场所这么近。但後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住了,有工人說,門房附近每晚有響動。呼啦啦地响,房顶上有踏步的声音,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地走,好像在徘徊。于是就搬了出去。我們當時也沒在意,反正我住在里院的正房,外院的门房有响动,我也听不见。有工人開玩笑說要找神拜拜,可是我没往心上去,许欢江也从来不露面,只是每月都把工程款打在卡上,所以一切工作都還都有序推進著。 再后来,有一天半夜我尿急,起夜去上厕所。老院子,屋子里是没有厕所的。里院也没有厕所,老旧的厕所设在外院的西南角,跟门房是对称的。本来,我在正屋里就放着一个空的脉动饮料瓶,用来接尿。可是那天恰好满了。只好拿着瓶子出来倒掉。可既然已经出来了,我心想,所幸就去外院上个厕所吧。 外院的厕所,还是那种很老的旱厕,在一个单间屋子的正中,挖一道沟渠,斜斜地通下去,直通到一个埋在墙外地下的大瓮中。人就跨蹲在这道沟渠上,秽物就沿着沟渠下去,积累在这大瓮中。快满的时候,就会有人在墙外把盖瓮的石板挪开,用木勺掏走大粪,用各种方式运出城去倒掉。 总之,很乱,很脏。而且这厕所不知道多少年了,估计从清代到现在就没有大修过,所以我一般不乐意过来上。 但今晚,月色很好,我于是就踱步过了中门,到了外院。悠悠地,能听到唱戏的声音,从远方飘来,是旦角的声音。很有意境。很久没有这么舒适过了,我本来是打算撒泡尿就走的,但既然这么舒适,不妨就拉个屎。 等到我蹲在那间古老的厕所里时,那唱戏的声音反而更响了。我心想,这半夜谁家唱戏啊。后来,声音渐渐地移到头顶: 良人浮梁买茶去,奴家守空船。 浮梁晋地千万里~ 绕船明月,江水寒~ 越来越不对,唱腔仿佛就在房顶徘徊似的,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一会儿远去,一会儿到头顶。我忽然想起工人们说的,门房房顶上有动静。我忽然吓尿了,连屁股都没擦,拉起裤子就冲出了这间古老的厕所。 我拖鞋都跑掉一只,冲进里院的正房,跳上炕,拉起被子蒙上头。慢慢平复心情。这才想起来自己没擦屁股,于是暗骂一声,起身找到纸,趴在炕上慢慢地擦。 再往后,我也就不敢在那里住了。 但工程依然要推进,许欢江依然见不到人。我就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家里到茶馆两头跑。 事情的真正爆发是在木工进厂的那一天。 木工为什么要進場呢,因為要做槅扇嘛,槅扇就是一扇一扇的木门,不要墙了,直接按每开间分,一个开间搞四扇窗户一样的木门。槅扇的一米高是裙板,很大一部分是用窗棂拼成各种好看镂空图案的槅心,槅心上裱纸或糊纱,不过现在一般都是安玻璃。这种槅扇其实并不保暖,在山西民居里很不流行。但是好看啊,所以通常在不住人的厅堂啊、庙宇啊能看到。故宫里的几乎所有宫殿,也都是槅扇门。 这处院子里,除了正房的第一层是闷房以外,都是明房。闷房就是很厚很厚的墙,前墙只开两个很小的拱形窗户和一扇门,非常保暖隔热,但是采光不好。明房呢,就是大窗户,矮窗台。因此闷房没法拆前墙,拆了就改变房屋结构了。但其他的房屋,包括正房的第二层明楼,全部准备拆除窗户和窗台,换成漂亮的仿古槅扇。也对,其他屋子的窗户也本不是原装的,而是建国以后重新搞的,非常丑陋非常破旧,我们当时把这个装修意见提给房东的时候,房东很高兴,连声说,就算你们不搞,将来他也要这么搞。 所以就拉进来工人,太阳还没露头就开动,只花了多半天工夫就把窗户都卸下来,窗台拆了个干净。然后请了一班木工师傅过来,开始做槅扇。 当我们把瓦砾啥的都运出院门,装车的时候,正是傍晚。忽然从东面来了一个老头。穿着蓝布褂子,拄着一个白拐棍,慢吞吞的。老头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说,这是要大动土啊!我们说对啊。老头又说,今天拆的墙?我们点头。然后老头说,你们供奉姜太公没有?我们很惊奇,怎么拆墙还要供奉姜太公?哈哈连笑几声,说没有啊没有。老头的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说,你们应该供奉一下的,本又不太麻烦。是要先选适宜动土的日子,在屋子的正墙中间,贴一张红纸条,上写: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然后上三炷香。就可以动工了。你要是不贴这个条子,就会很麻烦。这院子这么大,又这么旧,除了人以外,难保有些什么也附着生存着。院子当然是你的,你尽管改造。但你要动土动工,总归要通知一下人家吧?这是礼节问题,要是不知会一声就动工,万一伤着什么就不好了。这张条子就相当于是拆迁通知单。你拆,管你拆,但你要说一声。不能闷声不响地半夜强拆,这是要得罪人的。 你们这样不好,赶快补救一下吧。老头边说边摇头,然后朝西走了。不一会儿就不见影儿了。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都什么呀,拆都拆完了。算了,以后再有拆墙的活儿再说,这次只能先这样了。 把院子里都清干净以后,木工就能进场了。我们已经备好一根根解好的木料,就等许欢江招木工了。正当我要落锁的时候,忽然从街上来了一群人,抬着一个个的大箱子。大约一米长,半米宽,小半米高吧,看起来旧旧的,实木打造,用铜皮包着角,说是茶叶箱子。我凑过去闻了闻,确实一股茶叶清新。说许欢江许总已经买好茶叶了。要抬进来。我当时就愣了,这茶馆还没修好,就往里塞茶叶?这不合适吧。 再说了,这开的是茶馆,不是卖茶叶的茶庄。来一个客人能喝多少茶?用的着这么一个大箱子一个大箱子地往里搬吗?这把今后三年的茶叶都备好了啊,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茶馆都不一定能开三年。 我当时就准备打个电话给许欢江,问问。可是手机怎么也没信号。又一问,这些个茶叶都是付了钱的。也就是说我这里不用另交钱。那就放吧,爱放多少放多少,大不了弄错了再抬走呗。 我刚刚忙完,出了一身臭汗,于是就看着他们搬茶叶箱子。 正是夕阳非常好的时候,本来湛蓝的天空镀上了一层金色。我抽出一支烟来,点上。觉得生活简直不能更美好。 忽然就颳了很嚴重的一阵黑絮風。 風來得很詭異,刚开始只是天边的一条黑边,很快就鋪天蓋地。最先的时候,就看到这道黑边在南房屋脊上面,贴着蓝天生长,就跟无数根刺一样。紧接着呼啸声传来,然后才反应过来是刮风。 所有人都躲進了房裡。但大部分屋子的窗户和前墙都没有了,于是工人们就近躲进了门房。我则拼命往里院跑,跑进正房,准备把门一关。就在关门的刹那,闪进来两根人,吓了我一跳。我仔细一看,原来竟然是我父母!还没来得及问他们怎么来了,黑絮风也跟着来了。无数的黑絮一下次穿过门窗,落在地上。它们好像是有智能一样,在天上飞着,突然就想遇到一堵无形的墙,呼一下垂直而降,就掉落进正房里。一下子屋子里满地都是厚厚的黑絮。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门关上。长出一口气。抬头看窗外,,整个都是黑漆漆的,就跟深夜一样。我们于是把灯拉亮,心说把屋子里打扫一下吧,但是拿起笤帚来刚一挥动,带起的风就把黑絮吹得满屋子都是,根本没法打扫。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我和父母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相顾无言。半晌,我才想起来问,你们俩 怎么跑来了?刚刚没看到你们啊。父母回答说,我们过来搬箱子啊,刚刚路上碰到你们这个院子在进货,就帮帮忙。我当时惊讶了,你们搬箱子?!当时就用很大的声音在吼:小心身体吧,别瞎逞能!我们有工人呢,你们又不是工人。 可是吼完了呢,出又出不去。只好继续呆着。想起来问了问他们家里怎么样,他们说家里一切都好,门窗都关着。 后来忘了是谁提议,说我们睡觉吧。这个屋子里本来就有炕,是那种非常老的炕,炕沿的砖都被时光浸润成了光润深沉的黑色,而且被经年累月地上上下下的屁股磨得深深凹陷。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盘炕上出生、死亡。原本,我之前就在这盘炕上睡觉。但是自从几个月前听到了唱戏声然后逃跑之后,就再也没敢在这个院子里过夜了。但是今天呢,走又走不了,而且父母还在,再加上又困得不行,所以也就脱鞋上炕,睡了。 我們於是睡在炕上。我似乎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醒來時,我的父親母親仍在熟睡,但已经天光大量。我於是光着身子,蹲在炕沿上,掏出一支烟来点上,一边抽著煙一边看外面。外面陽光燦爛。很白很亮的光从天井上照射下来,从小拱窗看出去,有奇花异卉,各種花卉上掛著殘餘的黑絮。 我母親醒來了,她看起来非常疲惫,而且头发凌乱。她撐起身子,問我:夜這麼深了,還不睡幹甚麼。 我惊讶地问她,你没看到外面的天很亮吗?现在估计有十点多了吧,怎么还夜深呢? 可是明明陽光燦爛。我抬起頭望,發現雖然很亮,可是找不到太陽的位置和物體的影子。这时,外面忽然鼓譟起來,像是拨儿鼓儿挠儿一起响动,似乎是唱戏开场的声音。然后又有嘈杂的人声,在呐喊。又有拍门的声音,似乎拍的是院里的中门。我們於是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果然在惨白雪亮的院子里,有人在拍打中门。应该是那些木工们。 我打开中门,发现外院裡已经站了很多工人,也多了很多陌生的人。工人們都燃燒著火把,全都挤在门房口。火把的火焰在雪亮的白光下呈現透明,只有丝丝扭曲的热气升上来,很詭異。那些陌生的人有大人有小孩,高高低低的,穿著古舊的衣服,在工人的間隙站著。她們無一例外面容愁苦,較為年輕的單身站著,穿著奇異華麗的旗裝;稍微年長的帶著小孩站著,穿著偏襟大褂,也是面容愁苦;小孩則一臉茫然,頭頂挽著總角髮髻。我不知道從哪裡來了這麼多陌生人,只是慢慢地走下台阶,挪到门房口,跟木工们要了一根火把,也举着。父親母親也站在人群中。 我发现这火把竟然是用今下午刚刚运过来的上好木料点的。我一下就急了,揪住一个木工的领口质问:你他妈的知道这是什么木头吗?就这么点了?! 没想到木工比我还愤怒,他吼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木料! 周围人纷纷劝解,算了,算了。天这么黑,有这么大动静,大家都怕,不烧个亮光心里都害怕。 黑?又一个人说天是黑的。不,这么多人说都是黑的。那,我为什么看到的是白天?还有,这么多陌生的女人和小孩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一股凉意从背后涌上来。大喊一声,跑!然后就往大门口冲去。 没想到木工们把我拽住了,他们说,大门早就打不开了,要是能打开,我们干嘛不出去。 忽然遠處響起了急促的鼓點,就像是有一个名角要粉墨登场一样。大家忽然一起動了起來。但我发现,基本上是工人在追赶着那些陌生人跑。火焰熊熊,四处发抖。非常疯狂。 我起先是害怕,然后感觉自己的浑身都发热起来,好像刺出了无数的锐刺。我的脚几乎就要迈出去了,我转头看我父母,我母亲一直摇头,示意我,不要,不要。我想忍住,可是忍不住。战斗!战斗!我要战斗!我就不由自主地冲了上去,追着那些陌生的妇人和小孩在跑。我发现他们忽然掉转头冲我来了,我大吼一声,张开双臂,两只手捏成爪型,从他们的胸腹掏了过去。可是我发现只掏了一阵空气,什么都没有。那些人软塌塌的,飘来荡去,飘远了,然后又重新振作,又开始满院子飘舞、飞奔。我站在院当中,非常地茫然。我心想一定有什么不对,我于是抬起头来,看到门房上面的那块广告牌。牌子里那团乌黑浓密的头发仿佛更加浓密了,头发下遮着的半张雪白的脸,放佛勾起了笑容。我忽然呐喊一声。当时,我觉得我是飞起来了,尽管事后他们说我是飞快地拿了一把美工刀,极快地搬了一架梯子,极快地上了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仍然是飞起来了。当时我腾空而起,跃到广告牌边,手持利刃,利刃一划,有一团头发突然从广告牌中跌落,掉在院当中。 我从房上跳下来,刹那间满院飞奔的陌生人都停下了脚步,仿佛累极了似的,被抽空,瘫倒在地。躯体渐渐干瘪,就像是一堆破布堆在一起一样。我大声喊,燃! 我把手里的火把扔向了那团头发,工人们也都把火把都投向那团黑发。刹那间,满院子都是熊熊火光,头发燃烧起来了,那些破布也燃烧起来了。破布下面根本没有人,在火光燃起的那一刹那,天突然黑下来,四周漆黑,是一个正常的,午夜时分。只有院子当中默默燃烧的一簇簇火焰。 于是大门缓缓开启,所有人都默默地走了出去。我惊魂甫定,再也不想在这里呆着了。我四处寻找我父母,但是找不到。那些搬茶工人已经走得无影无踪。我绝望地掏出手机,发现竟然有信号了。于是赶紧打给我父母,那边响了很久才接起来。我非常急切地问,妈你在哪?母亲非常不耐烦地回答,在家睡觉!还能在哪!你小子成天不着家也就算了,半夜没事别打电话! 我感觉自己背后又千百万个爪子在抓挠自己,我拼命地向前奔跑,就像脚下的土地在无时无刻崩溃着、塌陷着一样。我本来是朝着家跑去的,但忽然家都不敢回。一时间在狂奔中茫然失措,不知道该跑去哪。最后跑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广场上,看着晚归醉酒的人,抱着灯柱过了剩下的夜晚。 第二天,消失了很久的许欢江突然出现了。 他在清晨打来电话,说是谈妥了一班木工,让我过去看看。我本不愿去看,可他一直催促着。我在电话里也没法说清楚问题,又想到大白天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疲惫地起身,打了一辆出租车,又返回茶馆。 我走进院子,发现院子里根本没有木料,只是还是拆得乱七八糟的样子。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木工,没有茶箱,没有那夜惊天动地的战斗。 许欢江站在院子里的阳光下,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笑吟吟地问我,找什么呢。 我疑惑了。 我走入房中,发现墙上裱着的草纸上的字迹全都变了。我原本是抄的琵琶行啊自叙帖啊,全部变了。而且字体也都变了,从草书变作极为清秀的楷书。我惊慌失措。抬头细细读去,上面写着: 妾本东城王家女,珠帘扮作娥女迟。 朱唇点绛绞金缕,嫁做商妇惹羞丝。 夫婿远去白云间,千帆绵绵江南驿。 茶砖铿锵玄铁色,高耸绵延如城池。 千乘万马临故里,春去归来暮秋时。 俄而旋走臀未热,驼铃声声走沙漠。 狼虎如山沙如斗,沧桑为我从天落。 白骨丛中循遗迹,蓝月星斗走冥国。 生撕牛马于中路,胡儿椒盐拌茶酌。 货来金玉邓通羡,压地银山骆驼驮。 夫婿来去赚辛苦,重重屋宇宅院落。 可怜贱妾冰簟冷,岁岁年华空房过。 从此怨恨茶与叶,惟愿人间不饮茶。 逢君难为千里水,便坏世上万人家。 谁人持茶从此过,听妾一曲断肠话。 何商何贾贩嫩芽,妾当一手狠勾杀。 莫言妾身无怜悯,当年悯妾有哪家? 伤春悲秋无限事,谁家流水承落花? 我左右回头看,发现阳光灿烂,但一个人都没有。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院子里也一个人都没有。 我大声喊,声嘶力竭:许欢江!许欢江!!许欢江!!! 26日晚,我和博文去参加北大的未名诗歌节。喝酒寒暄以后就误掉了地铁。离家太远,打车太贵,于是就到博文那里挤了一晚。当夜梦此捉鬼故事。翌日醒来,各种情节清晰,我以为奇。于是做此文。文中繁体字,是为当时梦中所见。 主播:莫大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cs/13624.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我,80岁,一定要离婚r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