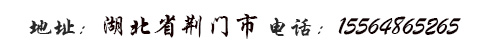寻找放逐的心灵散文
|
我所以用这张图片做为本文的开篇插图,是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是被称之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所以,我眼中最美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刘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心中永恒的英雄形象。 曾几何时,我很迷茫,因为时代的变迁,颠覆了我的审美初衷。我的心灵就像黄羊一样被放逐…… 今天,我开始寻找我的心灵,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圣神身份去寻找! 寻找放逐的心灵 1 我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坚硬的小镇。 这个小镇过去就是小镇,却没有这样坚硬。它叫河西堡,位于大西北甘肃永昌县,和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很近。 这个名很有意思,因为“堡”是和战争紧密相连的。就是在今天,这里依旧处处残存着战争的痕迹。 很久以前,这里有一条河,叫金川河。因为有了河,所以,远古的时候,这里就有人了,那还是在母系社会…… 我对这座小镇的最初记忆,是从五岁开始的。懵懂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波涛汹涌的绿色麦浪和山呼海啸般的黄褐色沙尘暴。到了冬天,狂风裹着小石子,打在脸上,小刀子割肉一样疼。 那时候我很小,能记住的风景,就是绿色的麦浪和冬天的沙尘暴。冬天的时间很漫长,似乎永远的冰封千里、沙尘呼啸的天气。出去玩,脚趾冻得像是断了一样。 于是就盼望春天早点来。 等待总是漫长或者遥遥无期,但是,春天总是会到的。每到春天来临时,封冻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土地,被黄牛拉着犁铧翻开,土壤蓦然感受到了空气的亲吻,把地心深处的热浪蒸腾而出,潮潮的热气合着草根的香气,在风明天净的大地上漫溢。 黄牛拉着犁铧在大地上行走,它被许多人簇拥着。“许多人”穿着黑棉袄或着光板子羊皮大衣,大敞着怀,光着脑袋或是戴着瓜皮帽,跟随着黄牛犁铧翻开的泥浪蹒跚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让人感觉到他们走出了一种气势,是什么样的气势呢?一时半会琢磨不出来,于是看见了女人。女人都包着红的绿的花围巾,红的绿的花围巾在河西堡这里,变成了远古骑士的头盔,这是因为河西堡的女人用一种奇特娴熟的手法把红的绿的花围巾包裹在自己的脸上,如果你把花围巾的材质变成薄薄的铁皮,和古代武士的头盔很像。所以,红的绿的花围巾把女人的脸整个包裹起来,只露出一双毛绒绒的眼睛骨碌碌转。 女人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包裹起来,像是柔软的馒头在蒸笼里蒸,那么,花围巾的里面,一定有一张水灵灵美丽的脸蛋吧? 男人或者女人,都簇拥着犁地的黄牛。 在春种的大地上,黄牛是主人。 黑黑的男人或者红的绿的女人,在粗粝健壮的黄牛身前身后,都成了陪衬。黄牛引领着黑黑的男人和红的绿的女人,在广阔的田野上把春天的使命用最为具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画成了一幅水墨画,这幅画很热闹,清爽干净。 春天的河西堡街道,算来算去,只有一条街,街上几乎每天都扬沙。扬沙的土街道在砂砾的苦涩味道里,像一幅在宣纸上晕染出的画,浅浅的淡褐色,让土木结构的门市部朦胧不清。越过拴马桩,按照透视的原理,远处的马路上,一架有着巨大轱辘的木质大车轰隆隆响着。骆驼拉着这架木轱辘车,在扬沙的土街道上缓缓地走着。车上好像没装什么,所以,这辆骆驼拉着的,有着巨大木轱辘的大车,似乎就成了专门为这条扬沙的土街道点缀才会有的一样。 赶车的汉子穿着光板子羊皮大衣,戴一顶羊毛帽子。“光板子”羊毛大衣就是拿羊皮直接缝衣服,一块块羊皮拼接起来,一直拼接成拖到脚底的长长的大衣。按说,羊皮的外面,应该吊一块蓝布或者黑布,叫做“挂面子”或者“吊面子”。也许是家里没有钱或者钱很少,所以,就不吊布了。原本是为了省钱,没想到这样的大衣穿在赶车汉子身上,那大衣上的羊皮,因了羊皮上的油腻,在风霜雨雪的浸淫下,羊皮的色彩已经是黑红色。黑红色的上面,又似乎永远的挂着一层煤粉,所以,羊皮的颜色是黑黑儿的。所以,那赶车的汉子,也就有了一种黑黑的威武气。 他和拉车的骆驼,似乎是一个整体,虽然他们不是一个整体。但是,骆驼高高的驼峰和一身深褐色的绒毛以及它野性粗莽的眼睛还有嘴角流出的乳白色涎液完完全全呈现出高大的意识,渗透进人的躯体里,能够感觉到生命的伟岸,能够让你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这一切,都被赶车的汉子控制着。他身上的重要标志就是那件光板子羊皮大衣。他有一双爱流泪的眯缝眼,这是沙眼。“沙眼”是西北人专有的“英雄病”。只有常年在刀子一般的沙尘暴里行走的人,才会得这种病。“沙眼”是医学术语。“沙眼”在西北人的嘴里,叫“迎风泪”。患有迎风流泪的人,应该是不简单的人吧。他的这双眯缝眼眼角上一直挂着泪水,和骆驼嘴角边的涎液很像。他掌控着一辆有着巨大木轱辘的大车。他给人的感觉,是掌控了一条街…… 这条街道,好像被一只巨大的手在沙漠和戈壁卵石中间抹出来的一样,一半凸显,一半又被沙子和卵石淹没。街道两边几乎没有建筑,前面说到的那个门市部算是“繁华”地带。门市部的墙面全是土坯垒葺的,是纯粹的黄泥巴建筑。黄泥巴黄色的墙面,和沙漠、戈壁浑然一体。尤其在春冬交接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飞扬着沙尘,朦朦胧胧的视线里,门市部大院的门前,进进出出着马车、驴车或者骆驼车。稀稀拉拉的人,穿着羊皮袄或者黑棉袄花棉袄,提着挎着,懒懒散散走着。站在高处,遥望河西堡小镇,沙尘弥漫,风像是醉汉,嘶哑着喉咙,狼一样地发出一种奇怪的低鸣声。整个小镇还没有褪去原始的野气,远处无垠放肆的戈壁滩,蔓延着一种浪涛般的气势,让这座小镇,随时就会淹没…… 那年的夏天下了几场透雨。下雨之前,连续的太阳暴晒,戈壁的卵石眼看着就要爆裂,一场大雨蓦然而至,卵石冒着白烟,大地蒸腾着地球的气味,滋润着劳作的人们的皮肤。小麦这时候开始孕育起波澜壮阔的浪涛,那时候,金川河也会涨满了水,奔腾着一直流向浩瀚的腾格里沙漠——那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来自祁连山的雪水,但是,漫漫无边的大沙漠,亘古不变的就是干旱和奔腾的狂风…… 小镇上有火车站,火车站地处河西堡小镇的最高处,站在这里,鸟瞰小镇,能看见远古时期的土庄子,厚厚的高墙,粗糙斑驳腐朽厚沉的大木门……这些土庄子建于何年,从来没有人考证过。离火车站不远就有一座土庄子,它高大的院墙,一如城墙般厚实。传说,这里最大的土庄子,土墙上面可以跑马,由此可见,这样的土庄子,一般的土匪或是官兵要想攻打进去,是要颇费工夫的。迄今为止,大家都忘记了土庄子的主人是谁?后来又到了哪里?很难想象,这样高大的土庄子里,过去住着多少人?又有多少风花雪月的往事淹没在时间的尘埃里。 后来,这个土庄子成了供销社的豆腐作坊,夏天的时候,因为大量的做豆腐,豆腐渣倾倒在庄子的墙角处,被猪拱着,臭气熏天。到了过年的时候,这里最热闹了。人们吃不起肉,吃豆腐也是凭票购买的,所以排了长长的队。那是腊月将至的时候,天气奇冷,买两斤多豆腐,等到排队到跟前时,脚趾也快冻断了。 镇上有照相馆,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来照相,黑白照片,每年都照,最后,照片多了,就用一个大相框子把各种各样的照片统一镶进框子里,照片上的人,很土气。这些照片,现在都可以当文物了。 过年总是要穿新衣服的,也少不了走亲戚串门的,街上依然有大轱辘车缓缓地行走,依然是扬沙的天气。穿着新衣服没走多远,身上就落满了沙粒。街上的小摊淹没在黄色的沙尘中,却依然挡不住女人们的馋嘴,沙尘弥漫的街道、花花绿绿的女人,一个小镇,飘逸着熏醋的酸香气…… 小镇上的人对醋有着不能割舍的感情,舌尖上的味道,如果没有了醋这一天干活就没劲。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醋,用的水是祁连山的雪水吧。在海拔米的雪峰上,所谓“祁连雪皑皑、焉支草茵茵”,金川河的水,来自祁连雪峰,所以,金川河的水,最早源自于祁连山,雪,是水的雕塑。这里有远古冰晶,在人类起源之前,这里就是冰封千里的雪域世界。几万万年前,这里的雪水滴滴哒哒,涓涓细流,千流百水,终于汇集成奔腾的金川河,从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峰高唱着生命的歌喉,所向披靡,一路冲刷出一条不算宽阔的河道,至此,这里就有了河。不论世界多么蛮荒,只要有了水,就会有生命。远古的人们,在河道两边芦苇结舍,草裙围腰,独木泛舟。遵循着母系群体的习俗,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自生自灭,又生生不息。 河水孕育了人类的民俗民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生命线就是河流的曲线,所有地名都与河紧密相连,水从雪峰顺势而下,绕山过峡,飞溅着浪花,一路冲出大山,头一道口子,叫南坝,接着往下走,就有了头坝、二坝、新二坝、上四坝、下四坝、六坝、八坝等地名。水是不能漫流了的,人们管住了水,水的走势,孕育出了一方水土生命的色彩。 生命的血液,因为雪山的挺拔融入了山野的气势,让这里的人,呈现出蛮荒的气质,更让这座古老的小镇,蕴含着野性的风俗——当我五岁来到这里时,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这里。也许五岁的年龄太小了吧?我望着远处的大山,我想,那里,一定有狼…… 2 许多年后,我在拍摄大型文献片《中国文化秘境之旅》时,上面描写的情景,都成了久远的回忆。今天,我在历史的碎片里,拼凑着回忆的画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这座小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河流的杀手,河流总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得干涸直到死亡。就像河西堡这座小镇,它的名字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它有一条河,一条流淌了千万年的大河——金川河。有了河,就会有人,所以,这里就成了人类聚集的地方;又因为有了人,这里就有了杀戮,于是人类把房屋修成了城堡。这个城堡位于大河的西边,所以,这地方叫河西堡。 所以,这里先有河,河是人类起源的先祖,更是文明起源的先祖。金川河流淌了多少万年后,这里才有人。所以,金川河是一条伟大的河。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见证了这条河流的消失过程…… 年,我从大秦之地西安来到了河西堡,那一年,我刚五岁。我从汉唐的圣地以懵懂未开的童子之身,来到了这个叫做河西堡的古老的镇子上。记忆里,在来甘肃之前,我是在距离西安市不远的一个叫做临潼的地方生活。在往前,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即便在临潼的记忆里,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是一座古老的村落和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是那座军用飞机场的子弟,但我却生活在那座古老的村庄里。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除了银色的战机以外,就是村庄的大槐树还有奇怪的黄土之下的沟壑以及沟壑里的院落和一些奇怪的人…… 所以,我来到河西堡小镇时,完全是白痴一样的一个小孩子。 懵懂的年华,眼望着一望无边茫茫戈壁,一如刚出巢的小豹子,许许多多的好奇心乃至疑惑让我在小心翼翼的步履中,有一种冲动,但是,我不敢。 到处都是孩子,我跟随着他们疯跑。终于来到了河滩,那是一条大河,水纹划动着优美的曲线缓缓地流着。好像没几天,这条流淌了几万万年的大河,突然消失了。河里的水似乎一夜就没有了,就看见裸露的河床突兀着成千上万的卵石,汪洋着残留的积水,正所谓水落石出。让我兴奋的是,河床里有那么多的鱼拥挤在浅浅的积水里,噼啪乱响。我们拿了脸盆随手抓鱼,很快就能抓满一脸盆。 我在懵懂未开的时候,见证了这条流淌了千千万万年的大河的消失。那么,这条河到哪去了呢? 它改道流走了。 人们用水泥和石头修葺了一条人工渠道,叫“工农渠”,河水从此被人为地管制起来,按照人们规定的路线流淌,就这样,一条大河没有了。 蛮荒的河西堡小镇,被人为的物质在迅速地改造。石灰石经过火的炼制,变成了水泥,地球上有了新的物种。于是,原本本真的小镇,有了水泥这种人为的物种变得坚硬起来。地心深处的石油,又经过火的炼制,变成了沥青,河西堡小镇原本飞扬着沙尘的街道,变成了柏油马路,新中国第一代解放大卡车开进了这里,慢慢取代了我记忆里的大轱辘车。这里有了发电厂,农民们第一次看见那样高的大楼矗立在戈壁滩上。其实,五十年代的高楼和现在的高楼比起来,也就是比平凡高了六七层,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高耸入云了。 今天,我手上就有一张那个年代的发电厂厂房,它淹没在汹涌的麦田里,并且麦田的汹涌波涛的涨势还没有停下来,随时随刻都能把电厂淹没…… 因为有了发电厂、铁厂、化肥厂……小镇上的那种粗糙的、似乎山野之风低吟断裂的乡音,也就不再是唯一的口音了。这里有了普通话。 我就是这个时候来到了这里。那是在年,我那年不满六岁。是懵懂未开的岁月。我来到了这里,首先看见了一条流淌了几万万年的大河的消失。我住进了楼房,听大人说,住在楼房里的人,都是有钱的人。我很自豪,因为,我住在高楼大厦里,并且,我家住在大厦的最高层——三楼。我每天爬在窗子边观看外面的情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条黛蓝色的柏油马路。这条柏油马路从小镇中心穿过,一直伸向遥远的大山里。那是一座绵延不绝的土褐色大山,山上几乎没有植物,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一蓬一蓬地,长势再葳蕤,也盖不住风化石松散的质感。在山的最高峰,魏然地挺立着一座烽火台。开始我不知道它是烽火台,更不知道是多年以前的汉长城烽火台。看电影《地道战》,知道了日本鬼子的炮楼,便以为那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是战后留下的…… 懵懂未开的岁月,看见的世界没有苦难,也许什么都没有,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记得我离开西安时,部队的人来送我们,他们都换了军装,肩章没有了,领章上面也没有了星星,变成了红红的一块。军帽上的星星也变了,变成了红红的五角星。解放军送我们去甘肃,还送给我一盒子有星星的肩章、领章和有星星的帽徽。整整一盒子——这些东西在我已进入老年阶段时,它们是那样的珍贵,但是,这盒东西,早已经变成了记忆里的烟云,都找不到了…… 所以,懵懂未开的日子是不知道尊贵的岁月。 年的河西堡小镇在瞬间里,让一条流淌了几万万年的大河消失的无影无踪。又在我懵懂未开的记忆里,把一座乡村小镇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小镇。我居住在有高楼的电厂家属院,家属院被一圈红砖墙密密实实地围起来,这样围起来,能把外面的野气挡住。 野气是什么?实际上,我从陕西来到甘肃时,纯乎是从陕西的农村来到甘肃的发电厂的。是从农村走进城镇的。我在陕西飞机场时,家是在陕西临潼的农村。所以,我从陕西来到甘肃时,是从农村进城了。有一点不同的是,这座叫做河西堡的重工业小镇,是我爹我娘他们把原本是乡村小镇,变成了城市小镇。非但如此,他们还在电厂的四周,修葺了一道红砖高墙,要用这种办法,挡住外面的野气。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初来到这里时,当地的农民让我有点害怕。他们的羊皮大衣和羊皮帽子之间,有一张冷漠的黑黑的脸。 我和他是在红砖墙外面不期而遇,他在柏油马路的那边,背后是汹涌翠绿的麦田。我颤颤巍巍地站在柏油马路的这边,背后是高楼大厦。我俩隔着黛蓝色的柏油马路。他为什么要站在麦田边我不知道,他看见了我,眼神很冷。整个面部表情,黑黝黝,好像上了油彩,闪烁着亮,浓眉之下,一双眼睛黑白分明,藏在羊皮帽子的帽檐下,让人觉得他很神秘。天很冷,我想,就算面前的柏油马路真的是条大河,这么冷的天,河也会结冰的。他照样可走过来把我…… 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对面的这位农民大叔要干什么?他那样冷漠地看了我好一会,也没有打算把眼光离开我,我害怕了,慢慢地回到了红砖大墙里…… 这种胆怯是每个孩子,尤其男孩子都要经历的,经历了一次或是两次之后,我的足迹开始向远方延伸,那时候的我很孤僻,不喜欢和他们扎堆玩耍。我有两个妹妹,虽然如此,我也不喜欢和她们在一起。我总是一个人跑出红砖大墙越过柏油马路一头扎进铺天盖地的麦浪里,感受小麦秸秆翠绿的气息。刚刚浇过水,灌溉沟渠上的杂草长疯了,翠绿的杂草中,有一种豆类植物开着粉色的小花,在满目的翠绿中,这种豆科类粉色小花,显得很妖冶了。这片杂草一直向下延伸,突然断裂,渠水向下跌落,砸出了一小片坑,蓄满了水,又经过一夜的沉淀,水面便灵动了,我看见一尾小鱼闪耀着银色光焰,迅捷地沉落…… 今天我想,我童年的记忆,也许就从这一汪深潭般的水开始了…… (未完待续) 刘刚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fb/11593.html
- 上一篇文章: 31所独立院校历年考题
- 下一篇文章: 奔腾男诗人方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