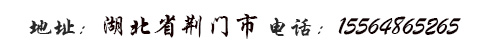瓦瓷滩
|
白脉软膏对外伤白癜风治疗效果如何 http://pf.39.net/bdfyy/bdfyc/170224/5231225.html -第篇- 作者:杨秀清 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杨秀清,女,年出生。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青年作家首届高研班学员,爱好绘画与写作,现供职于市群艺馆。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绘画散文集《有一座城市叫荆门》、中篇小说集《华隆女人》、长篇小说《张场恋哥》,目前已创作百万余字。 1母亲抱出一只一尺来高的坛子,说,这是当年你哥留下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淌出无数忧伤。她用手摩挲地着坛子,继续说,这只坛子真的好,色泽、形状,十几年了,它还是这样。 母亲慢慢地揭开坛盖,一股时光的味道荡出来。 母亲低头轻轻地闻了闻,说,明天,你就将它带给你哥。母亲说话的声音不大,轻轻地。轻轻地语调让我的心幽幽地疼,不知说些什么来安慰母亲。 母亲将坛盖盖上,如同抱着孩子一般地将坛子抱在怀里,说,瓦瓷滩窑厂的贺厂长那里还有一个,我想着终究是你哥的遗物,还是抱回来的好。 好。说完这话,那个我一直想要去忘记的瓦瓷滩,此时却像江水一般涌来。 瓦瓷滩是汉水边上的一个村子,经过历史变迁,演变成了一个管理着四五个村子的片区。远些时候,这里江水泛滥,长年冲积,淤塞成滩,滩地里又长了些芦草,看上去像一处蛮地。不知是在哪个朝代,来到这里居住的人发现滩边不远处高岭上的土,可以烧制瓦瓷之类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有了二者合一的瓦瓷滩之名。据瓦瓷滩上的老人们讲,皇帝朱元璋在为父亲守灵时,用的就是瓦瓷滩烧制的灯盏。灯盏点燃,孝期不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瓦瓷滩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交通位置,因为它处在汉水的中游和下游之间。瓦瓷滩北上有钟祥县城,南下有沙洋县城,解放前这些县城都没有修建大桥,因此处在两县之间的瓦瓷滩不经意间就有了热闹的渡口。当年红军从汉水东边过江来解放江汉平原,就是从不会引起国民党注意的瓦瓷滩渡口上的岸。年,政府在瓦瓷滩这里兴办了一家生产陶器的国营企业,不过是汉水边上管理着三四个村子的小片区,立马变得和城镇一样繁华,然后许多窑货就从瓦瓷滩渡口上船从汉水运输,北上南阳,新野,襄阳;南下潜江、仙桃、洪湖。 在瓦瓷滩,老师都会跟学生讲起瓦瓷滩的历史。我们的化学老师说,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透过教室的窗子,看到外面几十米高的三根烟囱正朝着天空吐出灰白色的烟。很快,这些烟钻进蓝色的天空中就不见了。我记得初三快毕业的时候,身为班主任的化学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们读书就是为了离开瓦瓷滩,走到外面的世界,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曾经生活过的瓦瓷滩是多么美好,它有渊源流长的汉水,它有发出清脆声响的陶器,它有高大的树木和好看的花朵,它还有那些散发着清香的泥土。听到这些话,我们一个个偷笑老师的矫情。 现在想来,确实如此。瓦瓷滩因为人的居住,久远前的荒蛮之地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变得秀美动人。北边的桃林,在春天开出烟霞般的花朵;西边的莲湖,在夏天开出娇艳的莲花;四季常绿的香樟、开着白色花朵的槐树、结着密实果子的桑树立在瓦瓷滩人家的房前屋后。 从瓦瓷滩渡口西行两三里路,就是瓦瓷滩街集。瓦瓷滩街集上的人家,多是依靠窑货生活,不是准备着板车帮忙拉货,就是有自己的私窑生产窑货,还有的就是国营窑厂的职工。有着数千年生产窑货历史的瓦瓷滩,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当地人谋生活的手艺。这门流传数千年的手艺,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这里的住户们赚了钱,就盖起了有别于其它村子的房子。青砖大瓦,飞檐翘角,前庭后院,许多房子都修建得都有大户人家的气势。 因为窑货的交易,这里有了人们日常需求的其它店铺:有炸油条、油圈的早点铺,有摆放着木椅的剃头铺,有燃着熊熊烈火的铁匠铺,有摆放着八仙桌喝茶聊天玩纸牌的茶馆,有挂着花色布料的裁缝铺;还有粮站、供销社……那些从远处到来进货的客商们,也会把远处的商品带到瓦瓷滩。这样,瓦瓷滩很容易触摸到城市的气息,城市里流行穿什么,用什么,这里也会有。这里的住户们要比附近村子的村民们要富足;这里的女孩子没有经过多少风吹雨晒,也比真正乡下的女孩子白净。 汉水下游的入处是省城的汉口,有人渡船来到瓦瓷滩看到这里热闹非凡,止不住感叹:瓦瓷滩像小汉口咧!瓦瓷滩的人很喜欢这个称谓,它带有强烈的表扬性质,很快瓦瓷滩的人就以小汉口自居。 我们瓦瓷滩就是个小汉口。我们瓦瓷滩什么都有。 去到老河口,不如看看我们瓦瓷滩这个小汉口。 …… 虽然瓦瓷滩是个热闹的地方,可是这里的年轻人还是不甘心留在这里,比如罗蒙蒙。罗蒙蒙是一个在瓦瓷滩长大的女孩子。罗蒙蒙喜欢听外面来的人,谈论起外面的世界,更喜欢听外面来的人讲起真正的汉口。罗蒙蒙听出来,真正的汉口与瓦瓷滩是有区别的,就连不远处的石牌镇与瓦瓷滩也是有区别的。瓦瓷滩到底不是城市。 年,罗蒙蒙正好18岁。这是一个女孩子长开了的年龄。 罗蒙蒙有一头长长的头发,她并不扎起来,也不是简单披着,而是在前额处的左右两边别了两个彩色的发夹,鼓出两个发髻。很多年后,当我看过电影《乱世佳人》,看到少女时代斯嘉丽的发型,一下子就想到了罗蒙蒙。不过,斯嘉丽的头发打着卷,罗蒙蒙是直发;斯嘉丽的眼睛是绿色的,罗蒙蒙的眼睛是婴儿般的嫩蓝色。那些从外地来进货的客商,有年轻的看到罗蒙蒙,就会主动与她交谈,交谈几句,见罗蒙蒙对城市感兴趣,就说道,要不有机会,我带你去汉口,那里可是真正的城市。 罗蒙蒙头上的发夹就是一个说话好听的年轻商人赠送的。那个年轻人还说,下次来就会为罗蒙蒙带来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年轻人看着罗蒙蒙说,你穿上,一定是瓦瓷滩最好看的姑娘。 罗蒙蒙带着妹妹罗荣荣去渡口等那个年轻人。两个少女坐在汉水边,身影美得像幅画。水风一阵阵吹来,霞光从她们的身后照到江面,看着涌动的江水,仿佛要把她们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罗荣荣问姐姐是不是喜欢上了那个年轻人?罗蒙蒙面带羞色,说,不是,我等他带来的连衣裙。 罗蒙蒙的父亲罗长发可不喜欢女儿与外地客商们走得过近,罗长发觉得那些人流里流气,不真诚。瓦瓷滩上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那些外地来的商人,花言巧语哄了瓦瓷滩的女孩子,最后女孩子肚子大了,那个商人却是不见了人影。女孩子就带着几个月的身孕,投到了汉水里。自古痴情女子负心汉,尤其是那些跑江湖的男人,嘴一张,四处撒蜜撒糖,四处惹祸根。 罗长发有罗长发的打算。 虽然罗长发有祖传下来的手艺混生活,但说到底,窑匠这门手艺还真不是女孩子们干的活。在罗长发那辈,上面有四个姐姐,只有他一个儿子,嫁出去的姐姐们没有一个完全掌握烧陶这门手艺。只有罗长发,从选泥、打胚到烧出成品,无不精通,并且打窑、修补陶器的活,他都会干。只可惜,罗长发膝下只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虽然都生得标致,但两个女儿都对烧陶不感兴趣。对烧陶不感兴趣的大女儿罗蒙蒙又不会读书,上完初中就呆在家中,跟在父母身边打打杂,跑跑腿。还在读书的小女儿罗荣荣也不想继承父业,她说她一定要读出去。所以罗长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为罗蒙蒙谋一个自己满意的上门女婿。 2我的家并不在瓦瓷滩。我的家在离瓦瓷滩十多里路的青龙村。 年的夏天,19岁的贺大为高考落榜,16岁的我中考落榜。父亲背着手在堂屋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我和贺大为跪在神柜面前,低着头,不敢出声。父亲的手上握着一根鞭子,像根尾巴似地在父亲的身后来甩来甩去。父亲在堂屋里每走两圈,就停下来,指着我们激动地说道,你,你——你们——。 啪,啪——,父亲从身后抽出鞭子在神柜上使劲地抽了两鞭子。声音响亮。父亲的鞭子抽得神柜打了颤。我也吓得打了颤。父亲用他那双充满红血丝的眼睛扫视着我们兄弟,然后举起了鞭子。在这紧要关头,贺大为勇敢地对父亲说道,我们去复读。 父亲终于落下半空中的手,说,我要你们俩兄弟对着贺家祖先发誓,来年一定会考出好成绩。就这样,我和我的哥哥贺大为在神柜面前,非常郑重地发誓。 啪。一个响亮而沉重地鞭子抽过来。 啪。又一个响亮而沉重地鞭子抽过来。 一个抽在贺大为的身上,一个抽在我的身上。 在那个热气渐升的七月,鞭子透过我们单薄的衣衫,刻画出一道深深的鞭印。父亲一字一字地说,贺大为,贺不凡,我要你们用疼痛记住今天的誓言。 第二天,父亲让我们兄弟二人和他一起到瓦瓷滩进窑货,然后到附近或者更远的村落叫卖。 破晓时分的瓦瓷滩已是人挤人,人挨人。拉板车的,推自行车的,挑担的。那些窑货像块布似地从坡上挂下来,又像块布似地铺在街边人家的院子里。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黄的,橙的,白的,赭红的,黄橙相交的……如此多的窑货,换作谁都会挑花眼。不过,父亲有他固定进货的地方,那就是罗长发家的窑货。 在瓦瓷滩,生产窑货最多的是林场边上的国营窑厂。除了这家国营窑厂,还有许多民窑。罗家窑货就是自己的民窑生产出来的陶器。父亲说,国营窑货喜欢远处来的大客户,而且它的价格也比外面生产的窑货要贵。走在集市的父亲,为贺大为讲解窑货更加细致。我曾猜想,是不是父亲的这些讲解,启发了贺大为对陶器的热爱,所以有一天贺大为把考大学的理想变成了去国营窑厂工作,做一名陶器设计师。其实在那天,我观察了贺大为的神情。贺大为只是认真地听,并没有流露出对陶器们的喜爱,那么是什么时候贺大为喜欢上了烧陶这个行当?一定与罗蒙蒙有关,一定是。 那天,贺大为在罗家窑货第一次见到了罗蒙蒙,我也见到了罗荣荣。罗蒙蒙长长的头发从发夹处顺着光洁的额头边垂下来,一直垂在她那鼓起的胸上。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衬衫,像一道好看的霞光。齐留海齐耳短发的罗荣荣虽然没有罗蒙蒙那般挺拨丰满,但因为时时充满着笑意的眼睛,脸上漾出一股又一股的甜。 罗蒙蒙没说话,两只嫩蓝色的眼睛里藏着些许傲气。罗荣荣的眼睛里没有傲气,含着纯真的敞亮气。面对两个好看的女孩子,我们俩兄弟都变得呆木起来。罗荣荣问,你们从哪里来? 青龙。我答。 父亲喊贺大为过去选货,我站在一边,看他们穿梭在一堆窑货里。 罗蒙蒙转身走了,留下我和罗荣荣。我站在那里,想看她,又有些不好意思看,又不知去跟她说些什么。罗荣荣到底是街集上长大的孩子,大方些,她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贺不凡。 在哪读书? 瓦瓷滩中学,今年刚毕业。 考哪了? 中专没考上。 还读不? 不知道。 那就读高中呗,读了高中考大学,你还这么小,总不能不读书吧。 …… 装好了货。罗长发喊罗蒙蒙出来倒茶。罗蒙蒙将茶水递到贺大为的手中,贺大为接过茶,仰天一口饮尽,他将茶杯递在罗蒙蒙面前,说,我能不能再喝一杯?那天早晨,没有吃早饭的贺大为连喝了五杯罗蒙蒙倒下的茶水。然后抹着嘴,对着罗蒙蒙展出了快乐的笑意。父亲在一边解释道,你看这孩子赶了十几里路,就渴得不像样子,真是没吃过苦。罗长发说,我看这孩子实诚。 临走的时候,罗长发走到贺大为面前问他今年多大了。 19。贺大为答道。 什么19,按虚岁都20了。父亲说。 罗长发意味深长地说,到了娶媳妇的年纪了。 那天,父亲和贺大为把一板车沉重的窑货安全拉到家的时候,父亲和贺大为的脸上都流出密实的汗。母亲为他们打来一盆冷水。母亲心疼地对贺大为说道,瞧把我儿累的。父亲用沾了冷水的毛巾迅速擦拭着脸、胳膊和腿,说,这算什么,我十五岁就开始下田挑谷咧。母亲没有理会父亲的话,对贺大为说,还是读书好,读书出息了,就不会做这个苦力活了。 父亲擦拭完,对贺大为说,吃完午饭,我们把货拉到西边的洪山岭去。 就这样,吃过午饭稍作休息的父亲和贺大为拉着沉重的窑货出发了。父亲嫌我碍事,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就免去了我前往的任务。父亲让母亲打一壶水来让贺大为带上。父亲看了一眼贺大为说,免得这犊子渴了就会把人家家里的水喝光。 那天午后,贺大为第一次与父亲辛劳地将窑货拉到三十里开外的洪山岭,再辛劳地用肩挑起那硕大无比的缸,一家一户的叫卖。但是因为一场雨,贺大为打翻了最值钱的大缸的缸内同样值钱的坛坛罐罐。 父亲又一次用鞭子抽打贺大为。母亲心疼儿子,拦住父亲说,你就是把他打死,那些窑货也不能完整。父亲说,我就是要他长记性。 因为淋了雨,受了急,又挨了打,贺大为晚上发起高烧。一天一夜,高烧不退。母亲流出了眼泪,呜咽着指责父亲。母亲说,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母亲跪在神柜面前,双手合十,虔诚的向祖宗和神灵们祈祷。 贺大为终于在第三天退了烧,人也清醒了过来。父亲对清醒过来的贺大为说,你不是卖窑货的料,等到九月开学,你就好生去读书。 我们全家怎么也没有想到,贺大为对卖窑货有一股不服输的劲。贺大为跑到罗家窑货那里,对罗长发说要佘窑货。罗长发从父亲那里知道贺大为打破窑货的事,按理,他是不会把窑货佘给贺大为。但是罗长发偏偏很痛快地答应了贺大为的请求。罗长发看到贺大为的身上有股子他喜欢亦或说是欣赏的劲。贺大为向罗长发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先不要告诉父亲。 罗长发拍着贺大为的身子说,放心。 就这样,贺大为用板车拉着小半车窑货独自一人从瓦瓷滩出发了。这一次,贺大为没有失手,而且卖得很顺利。 3贺大为把本钱交到罗长发的手上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贺大为对罗长发表达了谢意。罗长发听到贺大为的谢意,很是开心,执意要留贺大为吃饭。两人一边吃,一边开始打开话匣子。贺大为还谈论了他对窑货的见解。贺大为的见解很是让罗长发感到吃惊。他开始劝贺大为喝酒。罗长发认为,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更有味道。贺大为说不会。罗长发说,哪有男人不喝酒的道理,在我们瓦瓷滩,男人都要用烧出来的大碗喝酒咧,你看我们烧出的那些个坛子,就是用来装酒的。罗长发这么一说,贺大为就端起了酒杯。 贺大为有喝酒的天分,一口下肚,不烧心也不烧胃,倒觉得爽气。 就在那个七月的傍晚,就在那个罗家窑货的院子里,在盛开着红色、黄色美人蕉花边的小木桌子上,贺大为和罗长发喝起了酒,俩人越喝越亲密。罗长发依稀间觉得,他喝出了父子之味。就是那时,罗长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贺大为成为自己的上门女婿。 罗长发试探性地问贺大为,你觉得我家蒙蒙怎么样? 好。贺大为答。 哪里好? 哪里都好。 罗长发笑起来,端起酒杯,说,来,大为,咱们再喝一个。喝完,罗长发感叹了一句:这孩子,看着就让人喜欢。 罗长发还是带着长辈的责任,没把贺大为喝醉。他在贺大为走的时候问贺大为家中种了花生没有?贺大为说种了。罗长发接着说,你们青龙村的花生又大又饱满,现在又是新花生出土的季节,你能不能过两天带一些过来,我爱吃,这玩意下酒好。我家蒙蒙也爱吃,尤其是新出来的花生用盐水煮,蒙蒙最爱吃。 第二天,贺大为到沙田里扯了新鲜的花生,从根上摘下来,又选出饱满大颗的,洗得干干净净,装在簸箕里,端到母亲面前请求母亲帮忙做盐水花生。 花生送到罗长发的跟前,罗长发爽朗地笑道,好,真好。罗长发接着说,这俩丫头都跑石牌去了,我估计应该快回来了,要不你等等。贺大为看了看需要忙碌的罗长发说,不了,改天吧。罗长发说,好,我一定会对蒙蒙说,这些花生是你亲自送来给她的。 出了门,贺大为没有急着回去的意思,对我说,要不我们去渡口那里看看。我说,去石牌又不会走水路。贺大为看了我一眼,说,我只是想看看那些从外地来的船只。 远远地,我们就看见有船只的渡口。那些船上似乎只有人,并没有装什么货物。对生意人而言,是不会晚上在江上行驶,黑色的夜晚有太多不可预测和难以操控的东西,所以,货商们一般会在上午时分装好窑货出行。晚上,大都是从外地到来瓦瓷滩的客商,或者是要过到江那边或从江那边过来的村民们。 我问贺大为,汉水最后会流到哪里? 长江。 长江里的水又会流到哪里? 大海。 大海里的水呢? …… 贺大为不再回答我的问题,捡起身边的石子,十分有力地扔到江水里。像是要扔掉某种让他生厌的烦恼一般。 江水里不断有船只穿行,大船并不在瓦瓷滩停下,它们在江水里响起很浑厚的船笛声。 那些大船一定是开到大城市里。我说道。说完这话,我就发现船和笛声一下子远去。我忽然觉得,城市离我和贺大为真的很遥远。 在我们准备返回的时候,我看到了向江边走来的罗蒙蒙和罗荣荣。我兴奋地叫道,哥,快看,她们——罗蒙蒙、罗荣荣。 贺大为看到她们的到来,脸上的迷茫和内心的徘徊很快被江水漂洗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明朗和快乐。 那天,罗蒙蒙和罗荣荣俩姐妹都穿着碎花连衣裙,一个淡黄色花朵,一个淡紫色花朵。罗蒙蒙的黄色配着她成熟的身体,明艳动人;罗荣荣的淡紫色配着她的甜美,江风一般清爽。总之,两个人好看得像从画里走出来一样,又因晒了些太阳,走了路,两个原本白净的脸上泛出红晕。她们的美丽与身上的洋气味道,原本是离我们遥远的,现在是那么真实地站在了我们面前。在那一瞬间,我和贺大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慌张涌出来。 那天,罗蒙蒙和罗荣荣都很有兴致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看江水。霞光点点,江水涌流,很梦幻的场景。罗荣荣说,江上有城市,江下也有城市,所有的城市都会热闹过我们瓦瓷滩。 可是,瓦瓷滩也很热闹。我说。 瓦瓷滩泥土味太重。罗荣荣说。 如果你们都离开瓦瓷滩,这里会不会消失?我问。 罗荣荣笑起来,怎么会消失,除非汉水涨起来,淹没了瓦瓷滩。 罗蒙蒙和贺大为没怎么讲话,也许是他们年长些,不大好意思说话,只有我和罗荣荣两个,像两只鹊子,叽叽喳喳的。 天黑时分,罗荣荣邀我们去看戏。贺大为很开心得到这样的邀请。他问,什么戏? 罗蒙蒙说,不大清楚,只是知道是为我们这里的一个老窑匠过七十岁大寿。老人喜欢听。 去往听戏的路上,我们四个人很轻松快乐地谈了许多话。那天,罗蒙蒙也不像我们第一次见到的那样高傲,更重要的是,她会走在贺大为的身边。少女的芳香一阵阵地扑到贺大为的鼻子里,扑得贺大为忘记了许多东西,仿佛整个世界里,只有罗蒙蒙少女的芳香。 听戏的地方就在瓦瓷滩的戏楼。这座位于瓦瓷滩老街南边的戏楼,修建于清朝,几经风雨,依然存在。罗荣荣说,前阵子,这座戏楼还被老寿星出钱请人重新修整,所以看上去一点也不破旧。 瓦瓷滩里的瓦匠们有听戏的习惯。在清朝时,这里的窑货交易就有些规模,那些窑匠们在辛苦劳作之后,听一听婉转动人的戏,就会觉得所有的劳累都会散去。听戏的时光不是每天都有,一般都是民间一些重要节日,或是哪家娶亲嫁女做大寿。有时候,窑厂老板成功烧制了窑货,也会请戏班的人前来唱戏,以示祝贺。 台上小姐模样的女子轻声慢步地走出来,唱道:风吹杨柳条条线,雨洒桃花朵朵鲜,春风不入珠廉里…… 喜欢听戏的人听得入痴入迷。那个做寿的老爷子,身穿暗红缎花衣,坐在一方太师椅上,手放椅边,轻轻地和着拍子。罗荣荣说,老爷子是瓦瓷滩最厉害、最有资格的窑匠,就连现在窑厂的厂长都是他的弟子。 我们终究耐不住性子听下去。趁着好月色,来到了莲湖边。 月光下的莲湖真是美。虽然莲湖没有白天那般清晰,但也因这宁静皎洁的月色,让满湖的荷,多了些柔美。那些白天里的杂质,又都隐而不见,存在眼前的,只有高低交错的荷叶和荷叶里的花。白色的花在月色中,极显袅娜,有风吹来,叶子和花朵微微地拂动,舞蹈着一般。花和叶的清香一阵又一阵随风漾来。有一处水面,没有什么荷,在月光下,这处水面像镜子一般,倒映着荷与花的黑影,奇妙的是,这一方不足平米的水,还映出月的影子,看去,那天上的月亮仿佛掉进水里了。因为有了月亮,又把水拉得更为深远。 罗蒙蒙说,这里真美。 罗蒙蒙说完,贺大为吟了四句诗:蛙声喧夏夜,鱼影动荷塘。月染湉湉色,风抔淡淡香。这样的四句诗,在这样的时刻吟出来,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一瞬间,我为贺大为的才情感动起来。罗蒙蒙也在一边赞道,真好听。贺大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说,这是古人写的诗呢。 古人写的,你能背出来,也很好。罗蒙蒙再一次赞道。 罗蒙蒙对贺大为说,这里虽然美,但是我们女孩子还是不敢在夜晚来的。有了你们真好。 那是个多么美好的夜晚,雾气在流动,月光在流动,暗香在流动,一种叫情愫的东西也在我们心间流动。 4母亲放下坛子,嘱咐我早点睡。母亲说道,等你父亲赶回来,我就同你进城。 母亲离去,我依然睡不着。 睡在床上的我,看见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如同十三年前那般皎洁。透进来的月光正好落在坛子上,满屋子,仿若只有这个坛子。坛子上有幅十分浪漫的图案:荷叶连连,一弯月亮落在水中,图案边上有四个字——莲湖落月。贺大为曾对我说过,他要烧制一系列窑货,把瓦瓷滩最美的景色烧进去。事实上,他也开始这样做了。当年,他一共烧了四个样版的坛子,上面的图案分别是:莲湖落月、渡口飞霞、戏楼贺寿、美人争艳。我曾问过他,为什么是这些名字?他笑了笑,说,我是一个没有艺术眼光的人,说了我也不会懂。现在想来,贺大为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他不仅会画画,而且还有文采,不然怎么会取出如此好听的名字。 我看着这略带抽象的莲湖落月的图案,又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那个叫爱情的字眼啊。谁的年轻不会受陷于爱情,有的有了美好的结局,有的夭折,留下美好回忆,可是我的哥哥贺大为,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也在想,留在贺厂长那里的,是哪一个图案?余下的两个,都碎在了贺大为的生命里了吗?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赶往瓦瓷滩。母亲问我,要不要三叔用摩托车送我。我说,不用,小时候不都是走的吗?现在人大了,腿长了,应该更会走了。母亲说,这些年你到底是生活在城里,如此走路,怕是不习惯。要不走在路上,你看到什么车,就拦下稍你一段。 路还是曾经的路,又似乎宽了许多,平整了许多,路上还铺了些了石子。坡坡冈冈还是原来的样子,两边的房子也都是原来的样子。这些年,瓦瓷滩和附近村子里的年轻人,想着各种方法进城,这里的父母们也一门心思将钱供给想要进城的孩子,所以村子里就没有新的起色和变化。因为是夏天,没走多少路,我便热起来。我想起母亲的话来,这些年远离了故乡,所以故乡人擅长走路的事也做得不够顺溜了。终于来了一辆三轮车,可是我又不知如何去招呼,很快让车晃过去了。正懊恼时,车子在我的不远处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回过头来问我,是不是贺祖国家的儿子贺不凡?我点头。那人说道,快上车吧,刚才你母亲遇到我讲起你。 待上了车,我看清了是青龙村的贵伯,他老了许多,所以一时间我没有认出他来。记得那时,他有一个儿子在瓦瓷滩国营窑厂工作。他问我去瓦瓷滩做什么?我说,找贺厂长。贵伯叹道,贺厂长早不是贺厂长了,那个红红火火的厂子四五年前就没了。还没等我追问他儿子的去处,他自个说了起来,我那个在窑厂工作的儿子,现在也跑到南方打工去了。 我说,那挺好,现在年轻人都往南方去。 贵伯说,我儿子哪能和你比,听说你在大公司,还当着领导,钱又多,这回回来专门接老人去城里享福的吧?真是世事变幻无常啊,要是当年你哥一门心思去复读,或许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呢。 到了瓦瓷滩,贵伯掉转车头,说是要去石牌。贵伯说,现在的人都不兴赶瓦瓷滩了,需要什么都往镇上跑。 瓦瓷滩再也不是记忆中的样子。窑货也有,都是遗弃状地搁放在房前屋后,或是菜园边。几年前,塑料生活用品就取代了窑货。还在年的夏天,贺大为就提出过改进窑货的想法,他认为不改进,一定难得跟上时代。罗长发听到这样的话,笑着问,怎么改进?贺大为说,我也没想好咧。罗长发就对贺大为说,要不你就到我家里来帮我打打杂,我教你烧窑货的手艺,而且我还会付你工钱。 贺大为满口答应,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极好的事,学手艺还可以赚钱,更重要的是可以天天看到漂亮的罗蒙蒙。父亲对贺大为说,学手艺可不是三两天的事,难道你不去复读了?贺大为说,就算是去打零工赚钱,等到了开学的时间我自然就去上学。父亲不再阻拦,说,让你吃点苦也好,吃了苦就会珍惜上学的时光。 贺大为一来,罗蒙蒙就少了许多杂事,轻松了许多。只要是罗长发吩咐罗蒙蒙去做的事,贺大为就会抢着去做。贺大为说,都是粗活,该我们男人去做。罗蒙蒙就不做事,站在一边用一双嫩蓝色的眼睛看着贺大为,这样一看,贺大为就像打了鸡血似地,浑身充满无穷的力量。每天回来,母亲都会问贺大为,辛苦不?贺大为总是眼睛里流着满足的笑,说,不苦。 贺大为年轻,聪明,手艺学得很快。从选泥,到拉坯、造型、印坯、利坯、晒坯到施釉,贺大为比一般人都学得快。罗长发高兴极了,说贺大为是个窑匠的好苗子,他说如果有条件还要送贺大为到外面学习,增长见识。说完这话,罗长发就叹着气道,可惜了,你要考学呢。 看起来罗长发教了贺大为诸多做窑匠的技艺,但实际保留的多着,罗长发心里矛盾着,都教了也没有用,到底不是自己家里的人。然而他又是看出来了,贺大为是喜欢罗蒙蒙的。正在罗长发的担忧一天天逼近的时候,我的家中出了一件事——父亲挑缸卖砸了腿和脚,根不本能做什么重活。那时,田里的谷子正在渐黄,母亲的脸上因此布满愁色,成天也见不到笑容。 开学前一个星期的晚上,我和贺大为躺在床上。贺大为对我说,他不去复读了。 我问他为什么? 贺大为双手枕在脑后,靠在床上说,要是我们都走了,家里没个男人帮母亲干活了。 我说,不要把你说得那么伟大,你一定是喜欢上罗蒙蒙了,要在家里面娶她当媳妇。 贺大为没理会我的话,说道,弟,你去读高中,考大学。哥供你! 5我看似听了贺大为的话,去读了高中。其实也是因为罗荣荣,她说现在中专不招复读生,去读高中考大学会更有出息。罗荣荣说,她也会去读高中,让我在高中等她。罗荣荣还笑着说,要不我们以后考同一座城市里的大学,那样在城市里就不会孤单。我的心瞬间就温暖起来,也有了一种责任。我答道,好,就这样。 我记得那几天,瓦瓷滩蓝蓝的天空上,有都会一道长长的白色划痕,这道划痕正好穿过三根大烟囱。 罗长发听到贺大为留下来的消息,开心得不得了。他与贺大为畅快地喝了一次酒。罗长发从屋里拿出一本线装书,递给贺大为。罗长发说,这是祖传下来的烧窑的书,瓦瓷滩上的好多窑匠都想得到它,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是因为我已经把你当做自家人。过两天,我就去你家提亲,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我们家蒙蒙的。 过了几天,罗长发十分正式的到我家去提亲。罗长发对父亲说,提亲的事本该由男方先行,我先来是有原因的,我想让你们家大为成为我们家的上门女婿。父亲皱起眉头,说,这恐怕不行,再怎么着大为也是我们家长子。罗长发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更何况,你们家大为我是真心喜欢,我会像疼自己儿子一样疼着。 那个晚上,还睡在床上的父亲问贺大为,是不是看上了罗蒙蒙?贺大为点头。父亲失落地拍打着床板说道,早就知道你是这个原因不去读书了。今天我把话撂在这里,罗蒙蒙到我家做媳妇,可以,你去他们家上门,绝对不可以。贺大为说,不都一样吗?父亲生气道,肯定不一样。 第二天,贺大为仍旧和往常一样来到瓦瓷滩。 罗长发问贺大为,你父亲不反对? 贺大为说,现在婚姻讲究自由,我自己的事,当然我自己做主。罗长发的眼睛亮起来,说,这么说,你也愿意到我家做女婿。贺大为说,只要跟蒙蒙在一起,在哪都一样,其它的都是形式。罗长发听到这样的话,感动得快要落下眼泪,紧紧地握着贺大为的手说,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你,我绝对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 眉清目秀的贺大为在经过这个夏天之后,彻底黑了下来。黑下来的贺大为因为体力活也壮实了许多,但却失去了我自认为具有城里人潜质的儒雅气质。月假回到瓦瓷滩,在一堆泥坯前看到系着蓝布围衣,手上沾着泥巴的贺大为,我忽然间觉得他离我梦想中的样子遥远起来。甚至在某一瞬间,我从贺大为身上看到了父亲的样子。我伤感起来,哦,那个意气风发的贺大为,就这样一辈子了吗? 贺大为看到我,脸上没有露出一丝不开心,笑着招呼我,我很想努力地回报他一个微笑,或是和从前一样跟他斗斗嘴皮子,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出来。 我看到了罗蒙蒙,她似乎更漂亮了,倚在门边,拿着一面小镜子正在照着。罗蒙蒙穿着一件大红色马海毛毛衣,明艳动人,或者说像是一团焰火在那里燃烧。对,就是一团火,把罗大为烧得失去了自我。 回家的路上,我问贺大为,你真的甘心就这样吗? 哪样?贺大为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你就甘心一辈子呆在青龙村,呆在瓦瓷滩? 在瓦瓷滩也可以有梦想,有追求的。 呸,这个小地方还有什么追求? 我想做个窑匠。 窑匠?我想我没有听错吧,不入流的职业也叫梦想? 对,窑匠。贺大为的脸上露出认真而肯定的神色,我想做个新时代的窑匠。 我停下脚步,嘟着嘴,轻视地看着贺大为,说,你这个贪色的家伙!你,再也不是我贺不凡心中的贺大为了! 因为贺大为的放弃,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我想,我一定要读出去,我这个贺不凡一定要做给贺大为看,让他后悔自己轻而易举的放弃。父亲寄予希望的“大有作为”已经那样了,那么我这个“不同凡响”就该担起责任。 我的轻视并未改变贺大为的主意。我看出来了,他一心想娶罗蒙蒙为媳妇,然后继承他们家的产业,过一个简单的安康人生。可是,罗蒙蒙却没有顺从贺大为的想法。罗蒙蒙竟在贺大为和罗长发的眼皮底下,与那个年轻商人私奔。那个年轻商人每次来,都会绘声绘色地为罗蒙蒙讲述汉口的繁华;每次来,都会为罗蒙蒙带一些大城市里流行的东西。年轻商人说,蒙蒙,汉口的好东西多着,保证你去了之后眼睛都会看花,有机会,你真该和我一起去。听到这样的话,罗蒙蒙自然心动不已,但是她也会有顾虑。她咬着嘴唇,问年轻商人,那里的女孩子也一定很好看吧。年轻商人笑着说,好看的是蛮多,但是你一打扮,比她们个个好看。罗蒙蒙听到这样的话,脸上泛起红晕,本就漂亮的脸,让眼前的年轻男人看呆了去。年轻男人轻轻搂过罗蒙蒙,说,跟我走,我保证让你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罗蒙蒙到底是受骗了!那个年轻商人不但有了老婆,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并且,年轻商人并不是罗蒙蒙想像中的那么富足。罗蒙蒙带着满身的屈侮回到了瓦瓷滩。 此时的瓦瓷滩,对离开两月有余的罗蒙蒙早已是流言四起。罗长发将罗蒙蒙关在屋子里,狠狠地抽打。贺大为一把冲过去,夺过罗长发手中的筋条,抱着罗蒙蒙说道,我要娶罗蒙蒙。罗长发背着手,叹着气问道,大为,你,你不嫌弃? 不嫌弃! 我不同意。罗蒙蒙反驳道。 你?你还有什么资格不同意。眉目拧成一团的罗长发生气地问道。 我,我要嫁给一个吃国家粮的人,否则,我宁愿去死。 罗蒙蒙开出的条件,对贺大为而言,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然而,凡事都会有不可预料的时候。贺大为烧出的带有图案的陶器,被瓦瓷滩窑厂的贺厂长看中。他问贺大为,这些图案从哪里来?贺大为说,是自己绘画出来的,画的是瓦瓷滩的景色。贺厂长的脸色露出惊喜的光,他对贺大为说,可不可以烧出图案更精美的陶器?如果做得好,他就可以招贺大为去厂里做美工。这个消息,对贺大为而言,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贺大为满口答应。 贺大为开始了没日没夜的研究和制作。尤其是图案,他画了一稿又一稿。贺大为每天都会在瓦瓷滩里转一转,希望从中得到些许灵感。接着,选泥,打坯,勾形,上色,每一样他都全神贯注。贺大为知道,此次成功与否,决定着他这一生的命运。成功了,他不但可以成为吃国家的粮的人,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娶到罗蒙蒙。 然而,就在贺大为封窑看到希望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那场雨下得又大又长。三天三夜的雨,贺大为一直守在窑边,不敢轻易离去。开窑的那一时间,雨竟然停了。贺大为开心地想,这一定是个好兆头。贺大为亲手点燃开窑的鞭炮,啪,啪,啪啪——声音清亮,喜庆。所有的预示都是美好的。开了窑,贺大为娶出了一只:莲湖落月,色泽鲜亮,图案纹理清晰,形状圆润流畅,这绝对是贺大为目前为目烧出一最好的一只窑货。 真好! 真好! 罗长发也止不住夸奖起来。夸得贺大为觉得幸福像阳光一样铺过来。 我再去拿一只。 这只叫戏楼贺寿。贺大为为罗长发介绍。 这楼真像,还有这人,真是栩栩如生! 所有的窑匠对于自己烧出的窑货,都有一股不可言喻的疼爱和欣喜之情,它们如同匠人的孩子。罗长发和贺大为沉醉在这种喜悦里。 雨不知为何,又下起来,而且一阵比一阵急,一阵比一阵密,雨水落下来,发出啪啪的声音。 轰——轰——。罗长发和贺大为同时听到一种异样的声响。他们望去,窑坍塌下来。 我的窑货!贺大为发出尖叫声。 轰—— 贺大为向窑跑去。 大为。罗长发拉住贺大为,说,那里危险。 不——贺大为疯了一般向着窑跑去。 轰——轰—— 窑和窑里的窑货碎成一片,它们用碎片掩住了贺大为。 那一年,那一时,贺大为年仅二十岁。 6我终是在瓦瓷滩上没有找到贺厂长,听说他也搬去了石牌,这阵子和老伴一起前往城里带孙子去了。我能够猜想得出,当年意气风发,让人敬仰的贺厂长也一定风采不复当年了,和瓦瓷滩的窑厂一样老了下去。 我在罗长发的老家门前停下脚步。 一切旧去。 门口不再是盛开着好看的美人蕉,而是横躺着两个破损的大坛子。一个朝东,一个朝南。大气的青砖上,勾出斑驳的痕迹,砖缝间,长出几株野草。 门开着,我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走进去。 多少年了,我都想来看一看贺大为当年出事的地方;多少年了,我都不敢走进这里。就在进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背影。女子听到声响,回过头来。 是罗荣荣。 她变成熟了,也变得更加漂亮了,洋气了。她身上流淌的气质,已经与瓦瓷滩这个小地方一点也不吻合了。四目相对,共同惊讶。曾经以为,贺大为会娶罗蒙蒙为妻,我会娶罗荣荣为妻,然而一对阴阳相隔,我和罗荣荣也因为贺大为的离世未能走到一起。我所要忘记的很多东西,此时都翻涌出来,翻涌得疼痛。 你,还,还好吧?我开了口。 还好。罗荣荣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仿佛是曾经熟悉的样子,又仿佛很陌生。 你,你姐姐还好吧? 还好。 你呢?听说你已经结了婚。罗荣荣问我。 是的,你也应该结婚了吧? 暂时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女孩子不能拖太久。 我知道。 虽然我们隔着生分的东西,在有一句没有一句的问着,虽然我们这些年都没有联系,但是此时的我们,回忆到的点点滴滴,一定都与对方有关。往日时光里,我们都参与到彼此的世界里,可那又怎样?在贺大为离开的那段时间,我们挣扎过,也努力过,最终还是不能够走到一起。父亲说,罗家的女儿就是害人精,如果我和罗荣荣在一起,他就会在贺大为的坟前自尽。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我不可能再失去一个亲人,所以我妥协了。 我想起年的春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罗荣荣来到瓦瓷滩的桃林里。我们一起坐在桃树下,讲述着未来的梦想。那天,阳光明媚,朵朵桃花在阳光下比阳光还要明媚,罗荣荣的脸在桃花的映衬下,好看得无与伦比。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人面桃花相映红”。我们第一次在桃林里牵了手,第一次闭着眼睛吻了对方。我还举起了手,发誓这辈子只喜欢罗荣荣一个女孩子。 你要是喜欢上别的女孩子呢? 那,那就不得好死! 呸,呸,呸,太难听了。 那就考不上大学。 不,罗荣荣握住我的手说,不,我们都要考上大学,我们要一起去到外面的世界寻找精彩的生活和人生!说完这话,罗荣荣靠在我的肩头,向着远方的天空看去。那蓝色的天空,是多么广阔!足可以装下所有人的梦想。 想到这些,我情不自禁地对罗荣荣说道,对不起? 什么? 对不起,荣荣,当年是我不够勇敢,放弃了你。 罗荣荣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愿我们彼此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父亲一直想把它卖掉,但是我和姐姐一直不同意。曾经一直想要离开瓦瓷滩,如今是离开了,心里面装着的还是它的影子。 接下来是两个人的沉默。沉默之后,罗荣荣指着不远处的一处废墟说道,那里,就是你哥出事的地方。 我顺着罗荣荣指过的方向走过去。已经没有顺溜的路,所以,我必须高低起伏地走着,每走近一步,我就感觉腿脚沉重一分。我想起贺大为在这个院子里做窑货的每一个情境,他那时是那么年轻,是那么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明白,贺大为不仅仅是因为喜欢罗蒙蒙,也是因为为我们这个家。那次父亲脚伤得很重,在很长时间根本不能做什么重活,如果贺大为和我一样去复读,本就贫穷的家根本承受不起。所以,贺大为选择留在家中,担起了父亲该担的责任。为了我的生活费,贺大为时常挑着窑货去十里八乡的叫卖,甚至还有一次,贺大为让一只疯狗咬了,他没有在意,看了一眼伤口,继续挑着窑货叫卖。在罗长发的描述贺大为冲过去救窑货的场景里,我怀疑贺大为一定是疯狗病复发了,所以他才失去了理智,所以他才不管不顾地扎时塌陷的窑里。所以,我必须自责。 眼前碎土碎片。 我跪下来,慢慢掀开一砖一土。这么多年了,每当听到有人喊哥,我的心都会隐隐地痛。在后来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后悔,我为什么要轻视贺大为呢?他一直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他一直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他一直是个执着的人。我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一个贺大为,罗蒙蒙为什么就不喜欢呢? 其实,我姐是喜欢你哥的。 不知何时,罗荣荣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 我斜过头,看着罗荣荣。我知道,我的眼睛里露出了埋怨,我怨罗荣荣到了现在,还在骗我。 当年,我姐从汉口回来后,整个瓦瓷滩的人都在笑话她,只要她走到街上,就会有人对她指指点点,甚至一些年轻男子都来轻薄她。我姐知道,她这一生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所以,她有了轻生的念头。有一天傍晚,我姐跳进江水准备了此一生。我姐刚跳到江水里,你哥就赶了过来,他迅速跳进江水,将我姐救了过来。我姐之所以提出嫁给吃商品粮人的条件,是想让你哥退却,虽然我姐没有爱上你哥,但她知道你哥是个好人,不想连累你哥。可是你哥却从未嫌弃我姐,对我姐关爱倍至。我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也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渐渐地,我姐也爱上了你的哥,但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哥,所以她一直在矛盾。 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我问。 有。至少说明,你哥他也是被人爱过,他也拥有过一段他喜欢的爱情。如果,如果没有意外,你哥和我姐现在应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生活永远没有如果。我沉重地说道,罗荣荣,你的姐姐罗蒙蒙还在,而我,却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哥哥贺大为。永远! 7一直到后来,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哥哥贺大为在他最后的时光里,拥有过他所喜欢的爱情时光。那阵子,罗蒙蒙真心待他,他画稿,罗蒙蒙就坐在一边陪他,为他端茶递水。贺大为要去实景去看,罗蒙蒙也陪他。他们在瓦瓷滩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留下无数的欢声笑语。那阵子,贺大为的设计激清四射,而他设计的样稿内容,也大都与罗蒙蒙有关。 夜深了,陪在一边的罗蒙蒙睡去。贺大为便为她披上衣服,看着那么一张秀美的脸,贺大为止不住吻了过去。这一吻,便吻醒了罗蒙蒙。罗蒙蒙深情地看着贺大为,问,你真不后悔? 不后悔。贺大为说得十分肯定。 可是,我怕! 蒙蒙,有我在,谁也别想欺负你。 贺大为抱住罗蒙蒙,情愫涌动,他们再次吻了起来。 还是有人拿蒙蒙说事。贺大为一拳砸过去,把对方砸得鼻青脸肿。贺大为说道,从今天起,罗蒙蒙就是我的媳妇,谁要再说她的不是,我就要他不好过。高大壮实的贺大为,神情严肃认真,眉目里全然流露出不好欺,不好惹的字眼。也就是从那时起,关于罗蒙蒙的流言渐渐少去。罗长发慢慢展露出笑容,虽然女儿惹了事,但眼前的局势终归是好的。罗长发也不再保留自己的技艺,对贺大为和盘托出。罗长发心里盘算着,不管贺大为是否成为窑厂美工,入了冬,他就要为贺大为和罗蒙蒙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所有美好的构想,都在罗家窑坍塌的瞬间止步。 年的春天,我再次踏进瓦瓷滩。这一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离开人世。二十多年了,母亲一直叮嘱我,一定要找回当年放到贺厂长手中的画坛。 这一年的瓦瓷滩,已经看不到什么年轻人了,废旧的坛坛罐罐更加破碎。从老街穿过,除了几家新建的房子还有些生气,那些被锁住的旧门旧房,仿佛早已遗弃在久远的时光里。 三根红色的大烟囱还在,但许久没有冒烟,已经让人想不起它的作用。窑厂的两层职工楼,曾经是那么洋气,如今却灰暗破旧,七歪八斜在那里,变成了危房的模样。屋前,竟然还有两棵樱桃树,结满了橙红色的果子,它们饱满而水灵。也只有它们的存在,召示着大自然的美好在时光的岁月里,从未走远。也只有大自然的这些美好,还召示着瓦瓷滩的美好。我想,前阵子这里的桃林,也一定开出了烟霞般好看的花,还有那莲湖,也一定有月光落下。 就在这里,我终于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贺厂长。 贺厂长前些年就回到了这里,他说这叫叶落归根,人到了一定年纪,就格外怀念过往的生活,这里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他一定要回来。贺厂长抱出一只坛子,说,这是你哥当年留下的,听说这是一个系列,有四个,我也只是得到这一只。你看,这只叫戏楼贺寿。唉,戏楼也没有唱戏了。戏楼前不仅可以唱戏,在我们瓦瓷滩,还有窑匠节,过节的当晚,所有窑匠都聚在戏楼前听戏,端着大瓷碗喝酒,酒一喝,就把瓷碗砸地上,当——咣当——那声音,那气势,真是好。如今,再也没有什么窑匠节了。贺厂长慢慢转动着坛子,继续说道,当年,我抱来也是想着有人能够继续做下去,可是,唉,真是时代变化太快了,就是那么两三年间,厂子就垮了,人们都去用塑料用品了。红火了几十年的窑厂,不得不停业。从祖辈们传下来的手艺,怎么到我这就完了?我,我真是有罪啊! 时代的变化,谁也料想不到。我安慰道。 也是,不过我听说别处还是有窑厂,还是生产着窑货咧。 怎么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不会完全消失的。 我相信。我也希望瓦瓷滩回到曾经的样子。贺厂长望着眼前三根红色的大烟囱说道。我看见贺厂长的眼睛泛起点点泪光。 抱着坛子返回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叫瓦瓷滩的地方,安静得不能再安静,甚至可以听到一块老砖微裂的声音,可以听到一朵蓝色婆婆丁花绽放的声音。我知道,这个叫瓦瓷滩的地方,存放着多少窑匠人美好的回忆。他们在这里演绎着窑匠的艰辛与伟大,也在这里勾画出窑匠人的精彩。 人来人往,窑货满街。 依依呀呀,人生如戏。 渡口飞霞,人生如梦。 冰冷的坛子在我的怀中慢慢升起温度。这个温度,仿佛就是我的哥哥贺大为的温度。我将坛子紧紧地抱在怀中。 这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一个眉浓大眼的年轻男子,正在瓦瓷滩的街上走着,他的身边,是铺天盖地的窑货。 他抬起头,笑了笑,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 作者在瓦瓷 ——END—— 作者其他作品●石牌瓦瓷滩(组诗) ●留在故乡的人 ●寻梦石牌 ▼扫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cs/13962.html
- 上一篇文章: 有奖征集ldquo妈妈的味道r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