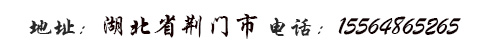徐本礼打狗原创首发
|
白癜风知名专家 http://m.39.net/pf/a_5941786.html 纯文学平台《红山草》欢迎您! 打狗 文/徐本礼 清晨,刘老五匆匆地用豇豆酸菜烫了一碗饭吃,就兴高釆烈地唱着丰收小调,挎上装香菇的背兜进城。他听人们说,县政府的招待所需要,就迈开大步走去。刘老五刚到一长排宿舍前,突然左脚被什么东西紧紧地钳住,随即疼痛难忍,直钻心肝。刘老五掉头一看,哎哟!腿肚子被狗咬住了。他一声大吼。狗掉头跑了。狗一跑,刘老五卷起裤脚,放眼一看,腿肚子已被咬去一块肉,血水长淌,大汗也随之满头淋漓。“血干命尽”这是刘老五听人们说的一句话。他怕自己流尽血,匆忙把背兜放下,把裤脚布扯下一块,将伤口紧紧的包扎。包扎的这块蓝布被血浸透,变得乌黑。刘老五咬紧牙关,忍受疼痛,狗还不满足,于是又返回刘老五面前。狗的再次出现,引起刘老五的更加愤恨,他弯下腰去,拾一块砖头,用右手高高举起,咬牙切齿,横眉竖眼,对准狗的脑袋,准备把砖头砸去,叫狗的脑袋成为粉沫!砖头刚要从刘老五的手中飞出时,对面突然响起炸雷般的吼声:“不准打!”吼声有如张飞断“桥”之势,一下子就制止了刘老五的行动,他把捏在手中的砖头缓缓放下。那人走到他面前,刘老五才奇怪的说:“这……这狗咬我,为什么不准打?”“咬你?”发出吼声的瘦高个子假装糊涂。为把证据拿出来,刘老五“嚯”地一下把裤脚搂上膝盖,露出血糊糊的包扎布,指着伤口说:“同志,你看嘛!”“唉!你怎不提防?”瘦高个子以责备的口吻,似笑非笑地说,“狗本来就是咬人的嘛!”老实本份的刘老五,以往难得进城,近几年进城的次数虽然增多,但路经还不很熟,变化又大,总爱走错地方。他听瘦高个子一说,似乎真有道理,原来装着一肚子的愤恨,却顿时消退许多。他呆呆地想:“农村的规矩是,谁被狗咬,谁就可以拾起石头或提着棍棒任意打狗,即使把狗打死,剥狗皮,吃狗肉,主人也不敢指责。在城里,很可能是规矩不同,狗咬了人,不仅不制止,还被指责。为什么呢?哦,小时候,他就听老辈人说过:“打狗要看主面。”在村里,支书家的狗、村主任家的狗就不知棍子和石头的味道。县城是更高的一层天,咬人的狗,说不定就是哪一个“大官”家喂的!刘老五想了想,心里乐观一些。伤口剧烈地疼起来。于是痛苦堆满面部。他又觉得,好端端的腿肚子,白白地被狗咬一口。实在划不过。莫说将狗打死、剥皮、吃肉,就是砸它一砖头,教训教训它今后不再咬人,也可解解心头之恨。自己正要动手,偏遇瘦高个子禁止!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凶?刘老五站着久久地发呆。瘦高个子站在间老五对面,借他发呆之时,瘦高个子仔细打量:刘老五头包白布帕,脸生黑胡须,上穿旧衣服,下穿大裤脚。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这一下,瘦高个子悄然大悟,彻底明白了:狗咬破衣人,刘老五是农民,所以被咬。刘老五认定,制止打狗的瘦高个子一定是狗的主人。他正要开口说点什么,长排宿命中有一道门“吱呀”一声开了。门声刚停,从门内走出一个发福的女人。这个女人站在门前,打个哈欠,伸个懒腰,随着抚弄一下爆炸式的卷发,慢慢抬起头,一边揉眼睛,一边对瘦高个咧牙露齿地说:“哦,是马科长,你才下班呀!”“是啊,是啊!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摄影:山人 “有哪样好消息呀?我昨天派小车去接冯县长,他今天就要回来了。”“是这么一个消息呀!”县长夫人不冷不热地说。刘老五在旁忍耐不住,“哎哟!“一声叫了起来。马科长听得叫声,狡黠地先看县长夫人一眼,挤了两下眼皮,指着刘老五说:“你家狗咬了这个老乡啰!看,还出了点淡血水哩!”“唉!我家的狗?这真是猫生狗崽——搞出怪来罗!我家狗从来没咬过人嘛!”县长夫人一边发唠叨,一边伸手抚摸狗头。“是啊,这狗从来不咬人!”马科长充当人证,忙把话题转过,把头掉向刘老五说,“老乡,也怪你太不走运呀!这大青狗是我给冯县长家小老幺用几千块钱买来的,来他家时就是一条半大狗,对它的脾气,我摸得很透,半年了,真的从没咬过人呢!”县长夫人拉长马脸走回里屋。大青狗咬到刘老五,县长夫人为什么要返回屋子?致使一向聪明过人的马科长顿时成了摸不着头脑的二丈和尚。马科长正在搜肠刮肚,千方百计说服刘老五,想让他不声不响地走人。在这紧要关头,为领导出力,不亏自己。这是马科长一向深有钻研的科目。他心里十分明白:自己之所以一下子被提为科长,就是因为自己手勤脚快嘴甜蜜。就是冯县长到省委党校学习前,他没有哪天不搞县长办公室的卫生、没有哪天不打开水、不倒痰盂……每次去做,他都注意观察,县长是口头上阻止,脸上却泛起挑花色的笑容。从而,马科长便得出一条结论:作为领导,谁不喜欢吹棒?在他看来,阿谀奉承就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把“吹棒”、“拍马屁”变成“尊重”之类的语言讨好。对,这就叫做“热爱领导”。他从官方那里得知,冯县长学习回县后,要被地区提拔为副专员。只要自己“尊重”冯县长,加上忠心耿耿、体贴入微的“服务”,到时一定会被带到地区,受到重用。他觉得在县政府行政科当个科长很不够味。只要如愿,尽管被那些“烂肚子”的文人骂为“叭儿狗”之类,也值得!“骂的风吹过,得的实在货嘛!说不定这大青狗咬老乡,正好给自己搭了一架天梯哩!”马科长想得心花怒放,想得眉飞色舞。口不读书,眼不识字的刘老五,好像不是大青狗咬了自己,倒是自己咬了大青狗。没人批准,就不敢离开。马科长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两人只好面面相觑。过不一会,县长夫人从屋内端着一瓶红得像血一样的水走了出来。她露出猪肝色的脸蛋,慢步跨到刘老五身边,抱怨地说:“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家这狗不咬别人,偏偏咬你,唉!究竟是你该倒霉,还是你的肉有香味哟!?来,过来!我只得把这上等好药给你用啰!”刘老五是第一次被狗咬,当然说不上用过什么好药。平时干活,手脚虽然经常破皮、流血,医院不太远,也极少用药。他被大青狗咬一口,本想打狗出气。谁知出面制止的是科长,这回为自己上药的又是县长夫人,似乎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还觉得是一种福气呢!刘老五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再次高挽裤脚,把头埋下,乖乖地看着伤口,根本不敢看县长夫人一眼。县长夫人一手拿药瓶,一手捏棉球。还未下手,她已看清:刘老五腿肚子上缠的那块裤子布,已把鲜血止住。在县长夫人看来,农民的皮扶就是好,抵抗力的强度非一般人可比!她断定:刘老五腿肚上的伤口不会发炎,更不会有破伤风之类的感染。说起用棉球擦洗伤口,县长夫人已积累经验,业务较为精通。按理,应将包扎的裤子布撕下来上药。但医院的大夫。她怕将布扯下,流血不止,收拾不住,便来个将事就事。她用棉球擦药,突然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孔弄得她差一点呕吐。本想将手缩回不擦,又意识到,血腥味的浓烈,正说明伤势不轻。要是不应付一番,刘老五耍起无奈,便难下台。县长夫人终于硬着头皮,把头歪向一边,把溅着药水的棉球,往伤口四周乱涂乱抹。红药水渗进伤口,刘老五额角冒汗,嘴里一边“哎哟!哎哟!”的哼,一边不停地叫喊:“这药水厉害!这药水厉害!”“厉害?你才知道厉害呀!”马科长把头掉向县长夫人,习惯眨了两下眼皮,才瞪着刘老五嘿嘿的冷笑说,“若不厉害,还能叫上等好药吗?”县长夫人擦了几下,便站在一旁。“哎哟!又出血了!”刘老五有些惊讶。“不止血!”马科长伸手按了按包扎布,“这是刚擦的上等好药嘛,怎会不止血?!”“上等好药?”刘老五像是不相信马科长说的话,又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认真的看着腿肚子说,“是血,是血,真的是血!”“哎呀!是血有什么可怕呢?狗的牙齿又无毒。你怎么像个小娃娃,见血就哭鼻子?我看,你这个老乡太没骨气,你没当过兵吧?没当过兵,你总从电影上看过在战场上负伤的英雄吧!人家手断、脚断、流鲜血,不是照样英勇杀敌吗?唉!你呀!你这个老乡……”马科长一本正经的给刘老五上政治课后,从县长夫人手中接过药瓶,拿在鼻子边一闻,眯眼、耸鼻、又闭嘴,用表情充分证实这真是“上等好药”。紧接着,他神秘地咬住老五的耳朵说,“老乡,今天你要不遇到县长夫人,谁会理你?你想,县长家的药水还有下等的吗?县长夫人又会轻容易给人擦药水吗?老乡,今天你虽然被狗咬了一口,还算是洪福哩!”刘老五仿佛深受感动,哆嗦着嘴唇,很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老乡,我再给你擦一擦。”马科长和蔼可亲,一边溅透药水,一边擦,一边还说,“老乡,你放心。这种上等好药,既消毒、又止痛、还长肉!不管怎么厉害的伤,用了它,几天就好!你知道这药是哪来的吗?进口的。进口,懂不懂?就是从外国买来的呀!”刘老五洗耳恭听,信以为真。马科长抓住这个机会,关心地对刘老五说:“老乡,你快走吧!要是我们走了,这里的狗还多哩!”刘老五如梦初醒,他惊讶地把头抬起,往那长排宿舍前看去。嗬!几道门前睡着几条狗。每条都是尖耳耸立,半躺半卧,头抬得很高,舌头伸得很长,眼睛也鼓得很大,而且都把目光投向他,特别是刚才咬了他的那一条大青狗,仍躺在县长夫人进出的那道门前,而且还是那么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它,不是狗,而是狼!是一只极其凶恶的会吃人的狼!看那阵势,只要动步,大青狗们就会不约而同,向他猛扑。甚至把他撕成肉片,吃下肚子!刘老五不由自主地筛起糠来,他在心里说:“天啦!要是再被咬,我的责任田谁种?我的香菇谁栽培?我的老婆儿女怎么办?那岂不是看着党的好政策,我刘老五也没法勤劳致富了吗?”可能是从助人为乐出发,马科长伸手提过背兜,给刘老五扶上背。这时,他看里面装的是香菇,做个顺水人情说:走,去招待所,我叫所长给你全买了。”刘老五挎上背兜,刚动两步,全身不停地冒汗,他很想说:“我要把狗打死!”但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伤口剧烈痛疼,张口却说出一个“我”字,就无下文。他痴呆地站了一会才说:“算了吧。只要不再被咬就算洪福齐天了。不打……打什么!”刘老五又困难地把脚移动了两步,刚把头一台,一辆轿车嘎然而止,停在他面前。车门敞开,走下一人。目光与刘老五相碰,却不认识。刘老五看他:头戴深蓝色的鸭舌帽,身披黑色呢子服,下穿黄色呢子裤,脚穿亮晶晶的黑皮鞋。身材魁伟、高大;面部严肃,仿佛一个将军。刘老五虽是愚笨,却能意识到他是一个大官,不是一般“星宿”。因而只敢偷偷地看!却不敢开口说上一句半句。这时,那人也仔细的端详了刘老五。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那被太阳晒黑的面孔,堆满愁苦不堪的皱纹。露出的腿肚子,血糊糊一片,包扎伤口的那块蓝布,血迹斑斑不堪入眼。“县长!”马科长上前甜蜜地叫唤一声,立即伸手去接黑色提包,冯县长不给。马科长虽没接到提包,仍是满面堆笑,充分发挥他轴承脖子弹簧腰的优势说,“县长去这半年,掉肉不少,瘦多了,学习真操心啊!”马科长的奉承语言,冯县长似乎一句也没听。他面向夫人,劈头问道:“这个老乡的腿肚子是怎么一回事?”“县长,嘿嘿!是这样:你家的大青狗把他的腿肚子挂了一块皮。我们已经给他擦了上等好药!”“上等好药?”冯县长紧皱眉头,“什么上等好药?”大青狗站了起来,抬头看着冯县长,尾巴摇个不停。它虽未见过冯县长,只因眼盯冯县长熟识地与马科长和县长夫人讲话,便模仿马科长的动作,摇头摆尾的迎上去,要邀功请赏!而且表现出洋洋自得的气派和风度。难怪人们常说:“牛马非君子,畜生也是人”哩!“这是谁家的狗?”冯县长问。“县长!嘿嘿!情况是这样的:你去党校学习,你家小老幺喜欢喂狗,是我给他买的。小老幺还真有一套驯狗的技术,这条大青狗被他驯乖了哩!”马科长像个技巧熟练的演员,伸手抚摸着狗的脑袋,以姿势助说话,表现富有感情。当他把目光触及冯县长时,因见不满才知失言。他灵机一动,又自然转了个弯说:“要是小老幺在家,这狗就不会咬这老乡啰!”冯县长再次看了看满面愁容,站地自己面前的刘老五,便弯腰拾起一块砖头递给马科长,命令地说:“把它打死!”马科长不敢多言,只好接过砖头,对准狗的脑袋,猛砸几下,狗还来不及跑,更来不及再摇尾巴,只盯着马科长,大叫几声:“告你家奶奶,告你家奶奶……”就四脚长伸,一动也不动了。狗被打死,嘴里、眼里冒着血泡,与扶持它的马科长和宠爱它的县长夫人永别了!冯县长把狗拖在一旁,拉过刘老五,伸手抚摸着他的腿肚子,又小心翼翼地把包扎的裤子布轻轻地揭开。只见伤处红肿,大似乳房,黑紫两色渗透,八个牙齿像八颗子弹穿过的枪眼。冯县长的脸色很严峻。他瞟了马科长和县夫人一眼。马科长和县夫人低下头,一声也不吭。“老乡,来吧!医院,上药,打针!”冯县长说着,把刘老五扶上了车。在车上,县长又对刘老五说:“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走了!”“不走?”刘老五打着寒噤说,“县长,我走,我走,我要走!”“你不能走呀!”冯县长轻轻拍着刘老五的肩膀说,“今晚和我一起吃狗肉,医院复查,如果真没问题,我送你回家。”“这……”“怎么?”冯县长笑道,“不愿与我交朋友吗?”刘老五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不回答。刘老五睁着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冯县长和马科长。尽管刚才还油嘴滑舌的马科长,现在的嘴唇却像上了弹簧锁一样。愣了好久好久,才像冬眠后的蛇醒悟过来,于是两步跨到车门边,说:“县长呀,我……我惭愧,都怪我给你添了不必要的麻烦。”(TheEnd.)作家风采 作家简介 徐本礼:男,年4月2日生,贵州省赫章县人,省作协、散文学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故事》、《山花》、《贵州日报》等30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万余件。作家佳作回顾 徐本礼:都是救命恩人 摄影师风采 摄影师简介 李春芳,甘肃天水人,笔名(昵称):乘物以游心,工厂工人,喜好摄影,习惯用纯净的心,畅游于诗海之中,用一部相机、一只瘦笔在俗尘写下彼岸,来寻找灵魂深处的栖息之地。投稿须知 一、作品须是原创首发文学作品,已在网络平台上刊发过的文章请勿投。体裁包括古体诗(五首以上)、现代诗、散文、小说(含小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随笔、游记、报告文学等,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可以连载。5天没有回复,请另投。二、每次投稿字数须在字以上,欢迎自带照片和配音。投稿前请仔细校对,文责自负。三、署名随意,文后附作者近期照片、简介和个人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fb/13605.html
- 上一篇文章: 书画装潢的形制品式
- 下一篇文章: 瑞安一老师在校长室里滋事并作出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