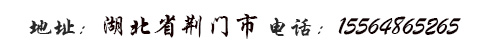消弥middot第六章银镯子
|
老家的除夕夜,大人是要彻夜守岁的,小孩子即使要睡觉,也不能脱衣服不能关灯。我回到家,把所有灯都打开,然后和衣躺下,把被子拉过头顶。里面一派鸟语花香,温柔得让人想哭,可是慢慢地,被子透出一股刚晒过的铁腥味,闻着像血。我爬起来把灯关了。熄灯的一刹那,楼下有车灯亮起,远光灯把窗框的影子打在天花板上。 我看着窗影从天花板跑到南墙上,然后消失,想起英木黎被抛弃的童年。正因为被残酷对待过,她才不吝惜弃人如敝履。无论陈骆安还是麦芒,都曾经深爱她,就算麦芒还活着,现在也会被她抛弃,就像她当年抛弃陈骆安一样。英木黎喜欢做第三者,喜欢伤害别人,喜欢看人被抛弃——可是陈狄安,他有家教良好的父母,有爱他的大哥和大姐,他的童年比英木黎幸福太多,我没法为他找任何理由。 大年初一,齐诺兰来我家,搬来一只叫“陷阱之旅”的椅子。 我一愣:“陈狄安回来了?” 齐诺兰没说话。 影子下来了,手里攥着当天的报纸,头版就是英木黎和曲谱在昆明疗养院度假的照片,她问齐诺兰:“你爸打算派谁去昆明?” “我爸,和陈导,通了电话。” 影子激动起来:“他让陈狄安去当狗仔队?我就不明白,英木黎有什么好拍的?之前麦芒没结婚,因为她比镜儿晚认识麦芒20年,你们就叫她第三者。这回倒是英木黎先认识曲谱的,只不过曲谱后来和别人结了婚,你们还她叫第三者?” 齐诺兰憋得满脸通红:“我爸,让陈导,问英,英木黎,有没有,隐情,要澄清。” “狄安去找英木黎了?”连影子都反应过来了,这是太明显的示好,齐老头这么做,看来还是想让陈狄安接手年度大戏。 我想,陈狄安一定是回来了。 大年初二,齐诺兰又把一张双人床搬进了我家。 我把工资卡塞给他:“密码还是原来那个。” 齐诺兰接过卡,在床沿上划一下,新床垫上的塑料布“嘶啦”一声裂开了,他把塑料布撕完就走了。我追到阳台里,陈狄安的车正打转向出小区。 第三天,齐诺兰又来了。我开门时,他正把一张躺椅搬出电梯。躺椅长,尾端的三分之一还卡在电梯里,影子听见电梯警报,跑下来帮他一起搬。 我眼里的齐诺兰和影子,渐渐模糊成去年冬天,收房时的陈狄安和我自己。原本我和他的未来里,就有这样一把草绿色的躺椅——这张躺椅,这张双人床,这把“陷阱之旅”,都是我和陈狄安一起看过的家具,这些都是在他的书房拆掉前,我喜欢而我家怎么都放不下的家具,这些都是他许诺过,婚后会出现在新房里的家具。 第四天,齐诺兰一按门铃,我直接坐电梯下了楼。 齐诺兰看见我吓了一跳,指指后备厢说:“你,你搬,搬这个吧。” 没有陈狄安,没有陈狄安的车,陈狄安好像算准了,故意让我扑空。我满腹狐疑地跟在齐诺兰身后,把餐桌和餐椅搬上楼。 一开始,齐诺兰想把躺椅放在南墙根,放过去才发现,椅背太高,把墙上的电视挡住了。于是他把双人床推出一米,把躺椅竖着塞进床头和阳台门之间的夹缝里,可惜躺椅太长了,又把阳台门挡了个严实。齐诺兰倒是不气馁,马上把躺椅拽出来,把床重新推回去,接着把躺椅摆在了床尾。 眼看卫生间的门被躺椅堵住一半,我赶紧说:“就这么着吧,我可以去影子那上厕所。” 齐诺兰不说话,开始把躺椅往餐厅里搬,最后四只餐椅惨遭淘汰。 “还有这个,”我把浴缸里的“陷阱之旅”拎出来,“不是我不要,实在放不下。” 齐诺兰把“陷阱之旅”拎到门口,看起来要走了,又折回来浇了遍兰花。 我送他到楼下:“你让陈狄安别躲了,他想回来就回来,用不着等我爱上你,我爱谁跟他没关系。” “我知道,”齐诺兰破天荒勇敢起来,“你就像你家,我就像这些家具,无论怎么放,总是差几厘米。” 第五天,齐诺兰没有来,可是天刚擦黑,我就在楼上看到了陈狄安的车。 我受不了了,下楼直奔他而去:“你他妈的有病吧?” 当我拉开车门,看见里面的人是陈骆安,我彻底冷静下来——程真,其实你了解陈狄安的,他是那种无论第几次和你谈恋爱,都能把你当初恋的人,他那人忘性大,喜欢谁都像第一次,你怎么能指望他旧情难忘。 突然,我小腹一抽,我又感觉到“她”了,可我不敢让陈骆安看出来,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对陈狄安还有幻想。 陈骆安下了车:“阿真——” 影子缩着肩膀从楼里跑出来,把手机递给我:“齐老头找你。” 我听见齐老头说:“你让狄安回来吧,《霍乱之乱》入围了欧洲电视节,这是台里第一个国际大奖,要是没人去领,谁脸上都不好看,你想想办法。” 我说:“为什么非得是我?” 齐老头:“如果他不回来,我只能批他辞职,让你去领这个奖,你还记得你是他的副导吧?” “好,我去领奖,哪个国家,我明天就办签证。”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他妈的为什么要辞职?我就是受不了别人老是把我和陈狄安绑在一起! “你说什么?” “我说我去,你批他辞职吧。你以为我怕陈狄安觉得,我在报复他?还是我怕别人以为,这个奖是他给我的遣散费?我不怕,齐台,除了再跟他发生关系外,我什么都不怕。” “大哥!”影子叫起来。 我抬起头,看见陈骆安顺着车门矮下去,倒在雪地里。我跑过去,想把他拽起来,可他身上哪哪都是凉的,袖子上都结了冰,整个人硬得像一具冰雕。我不敢再碰他,挂了齐老头的电话叫救护车。 影子冷静地跪在雪地里,开始翻陈骆安的衣服,很快从他裤兜里摸出一个小铁盒。她从铁盒里倒出两粒胶囊,塞进陈骆安嘴里。没等我问是什么药,她已经开始扇陈骆安的耳光,一直扇到他嘴唇松动,可以徒手掰开。影子两手掰着他的嘴,叫我往里倒水。我拧开一瓶水,头两口还对得准嘴,后来倒的全进了陈骆安的脖颈——我忽然毫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关心他什么时候能醒来,他为什么会晕倒。我意识到,影子的熟练、影子的临危不乱,直接指向一个问题——她知道的我不知道。 陈骆安喉结一翻,药下去了,他很快恢复了意识,在影子的搀扶下站在我对面。我看着他们似乎很熟悉,却又很陌生,我有无数问题要问,却不知道从哪问起。 救护车不早不晚地赶到了,陈骆安上了救护车,影子还想跟着去,被我伸手拽住了。救护车的后车窗被蓝布挡着,所以目送陈骆安,并不如电视剧里目送囚犯一样写意,我目光冷冷地落在影子身上。 影子浑身一颤:“你不担心大哥吗?” “陈狄安到底怎么回事?” 影子:“这关狄安什么事?” “陈狄安回来了,是不是?” 影子:“他不可能回来。” “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影子不作声。 “影子!” “——大哥得了和大姐一样的病。” “什么?” 影子低下头:“狄安只是怀疑,还有很多症状对不上,但大哥学了11年医,他想瞒谁都不难。” 难道陈狄安非走不可,是怕再次面对死亡?难道陈骆安和大姐一样,也要死了?我像个卡壳的碟片,不停重播着大姐寂然倒地的画面——不,不,陈骆安不一样,陈骆安和大姐不一样,陈骆安从来没有让弟弟失望,陈骆安甚至从来没结过婚,他永远不给女人把他变成庸俗男人的机会。 “如果是家族遗传,”我被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吓了一跳,“陈狄安会不会也得了一样的病?” 影子忍无可忍:“你明明看到大哥晕倒,为什么非要把对他的担心,转移到狄安身上?” 因为我看不到陈狄安,因为陈狄安去了一个我看不到地方。 影子:“大哥刚才的症状,和大姐——你别再否认了行不行?大姐第一次发病时,只有你在她身边!” 那又怎么样呢?就算陈骆安得了和大姐一样的病,那又怎么样呢? 影子:“大哥恐怕早就知道了,要不是他时日无多,他说什么也不会让狄安知道。” “知道什么?陈狄安知道什么?” ——“大哥爱你,英木黎之后,他只爱你。” 我震惊地看着影子,就像冬末绽放的雪花震惊了春天——陈骆安? 回想和陈狄安交往的四年里,我和陈骆安当然有过交谈,有过独处。我还记得前年平安夜,陈狄安在外地拍戏,陈骆安教的大二女生,因为对他表白不成离校出走了。我陪他在大雪里一路找一路说话,我惊异于他并不着急,他承认他并不想找到她,因为“我要是女学生,让男老师这么一找,不爱他也觉得爱上他了”——他相当懂得爱,但他始终跟爱情保持适当距离。陈骆安对于我来说,甚至跟齐老头一样,是上一代的人,一个丧妻的孤单男人,一个传说,一个情深不寿的短命鬼。 陈骆安真的要死了? 大雪在我和影子之间疾速下落,她的脸开始变得无比遥远。我想起陈骆安那张跟谁都像隔着一场大雪的脸,想起陈骆安把我带到英木黎跟前,告诉她:“这是程真,大姐一直觉得她像你,想让你见见她。”想起在墓地里,陈骆安双手捧给我一只盒子:“大姐的遗物,还有,我现在要完成她的遗愿。” ——大姐的遗物! 我像一只被雪活埋的小动物,突然冻醒了,从里到外结结实实打了个激灵。我忽然意识到,大姐留给我的遗物,我还从来没有打开来看过。我拽着影子上楼,意识里只剩下遗物、遗物、遗物,这两个字像一个囚牢,拆掉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它。 可我真的不记得把它放哪了。我拆了墙,换了家具,我流了产,住了院,在机场晕倒——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像一根皮鞭,把我抽得像一匹惊马。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是一只大红色的盒子,见方,巴掌大。 我跪在地上乱翻一气,所有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茫然起身,脑子一片空白,房间里的灯开了又闭,闭了又开。雪还在下,顺着雪花飘落的方向,我看见落地窗的把手上挂着一只双肩包——我忽然就看到葬礼那天的程真,她背着这只包,身后是雾气一样绵延的墓碑。我拉开阳台门,拉开背包链,那抹红色就像有生命一样,马上蹦了出来。 我握住它,抚摸它,温暖它,待它安定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盒子里面,睡着一只银镯子。它表面光滑无痕,没有一点花纹,甚至连镯口都没来得及封上,看起来非常像希腊字母Ω,豁口上一边一颗锈色珍珠。我试着把手从镯子里穿过去——穿不进去。 我是变得巨大无比的爱丽丝,再也回不到来时那个大雾弥漫的洞口。 齐老头又打“你确定你要去?我可让人给你订机票了。” “我——”眼泪落下来,打在银镯子上。 齐老头:“领完这个奖,你三年都不能辞职,听见了吗?这不是万的事了。” 我哭出声来:“你去找陈狄安,你找他回来,你为什么不能找他回来?” 齐老头:“我敢吗?你和他之间,老头子我选你。” 可让我选一个人去死的话,我会选陈骆安。陈狄安,我救不了你大哥。我摩挲着手里的银镯子,想起那场伴随着大姐倒地而消失的日全食。 ——“阿真!” 我听见大姐在身后叫我,可我急着回家,没有回头。我怕陈狄安醒了找不到我,怕陈狄安发现我早上四点陪大姐上早市,怕他怪我纵容大姐的婆妈和市井,更怕他说“你和大姐不一样”。我喜欢大姐,喜欢她身上与世无争的灵光乍现。陈狄安对大姐的不屑,总让我感到不安。 我坐进出租车,回头就看见大姐的头遮住了整个太阳,一时间天昏地暗。她像被风吹歪了的树,身子顺着风向,往后仰去。她每仰一点,太阳就多露出一点,最终,太阳跳出她的头颅,天完全亮了。大姐静悄悄砸在地上,脸上没有一点痛苦,好像走着走着,突然落入了另一个时空。 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等她,没有帮她把太阳关住。她像手中沙,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不在手中。陈狄安,我救不了你大哥,我救不了任何人。 影子把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你看英木黎戴的镯子。” 英木黎左手腕上的银镯子,和我手里这只一模一样。 影子说:“英木黎不戴这镯子很久了,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戴的?究竟这只就是她原来那只,还是这两只镯子是一对?” “阿真,”齐老头突然说,“回来拍《英木黎》吧,狄安当初走,就是想让你留下,前几天我和他通电话,他说只要你拍,版权他去和英木黎谈……” 电视里的声音冒出来:“腊月二十九,英曲飞抵昆明,同车前往疗养院。入住当晚,二人彻夜长谈,一室共进早餐。接下来三天,英曲均未现身公共区域。入住第七天,也就是今天下午,英木黎约见妇产科医生。” 我忽然明白了——英木黎怀了曲谱的孩子,这才是陈骆安晕倒的原因。陈骆安不可能爱上我,就像陈狄安不可能把我托付给一个要死的人。 我上网一看,“曲谱七天快枪手”、“英木黎首启生殖系统”等黄段子已经新鲜出炉。怪不得陈骆安哀莫大于心死,原来麦芒死了,他还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两个人之间是很奇怪的,麦芒在遇到英木黎之前,一直是不婚主义者,他18岁和镜儿谈恋爱,谈到38岁都不肯结婚,而英木黎和麦芒结婚7年,一直是坚定的丁克,现在倒要给曲谱生孩子了。 我决定去探望陈骆安,医院,值班大夫说他已经走了。我只好去找大姐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陈骆安早年在北大的师兄。显然师兄也听说我和陈狄安分手了,见到我非常惊讶。他告诉我,陈骆安的确在大姐去世后,找他要过相关的诊疗记录。 “安安的去世,给骆安刺激很大,我想他大概是想搞清楚,这种突发病和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十年前,他放弃临床心理转去学中文,对系里、对他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你知道吗,他博士后的立项是‘偏执型人格障碍后天满足的治愈机制’,这在当时相当具有开创性——” 我说:“是大姐有人格障碍?还是大哥有?” “安安她,”师兄犹豫了一下,“安安有分裂型人格障碍,她博士毕业后不能工作,就是因为这个病。后来狄安和她闹那么僵,不能全怪狄安,她一个每门功课都考第一的天才学生,突然开始讲特异功能,搁谁谁都受不了——” “大哥为什么瞒着我们?为什么大姐自己也不说?”我突然想起,大姐说她没有痛觉,是铜墙铁壁的一个人,我一直以为她是安慰我,怕我们担心。 “你别自责,看不出来是正常的,而且安安一见你,就把你当发小,说你像英木黎。” 又来了——大姐说我像英木黎,你们说大姐有精神病,如果大姐真有病,你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病人的话? 我说:“大哥随身带的药,是你开的吗?” 师兄摇头:“如果他也是这个病,我不会给他开药,不会让他住院,更不会叫他来确诊。” 这个病是没救的,陈骆安显然自己也知道——想到他15岁上大学,25岁博士毕业,本科5年、硕博连读5年、外加北大六院实习的1年,一共学了11年心理,后来为了一个英木黎,他冲动地弃医从文,英木黎嫁给麦芒后,所有人都以为他完了,后来还不是留在中文系当了老师?他的人生比谁都容易,他的人生也比谁都艰难,所以,他是不是早就不再留恋了? 我在口袋里攥住那只银镯子——大姐,我该怎么办? 凌晨四点,医院走廊上的人开始多了,我终于拨出了陈狄安的电话,如果他还在洛杉矶,应该正在吃午饭—— “Hello?”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控制住问她是谁的冲动:“I’dlikespeaktoChen.” 我听见陈狄安走过来,他一步一步地,穿越日月星辰,穿越江河湖海,我们之间离得这么远,是安全的—— “陈狄安。”我又一次,把这个名字说出了口。 他马上挂断了电话,我耳边的忙音越来越大,从此没人找得到陈狄安。 我终于可以肯定,陈骆安是真的命不久矣,想让陈狄安回来,除非是陈骆安的葬礼。他对大哥大姐如出一辙,他们陈家人,从来不讲什么惜别。 我从长椅上站起来,丧失了探究答案的勇气。陈狄安做了第二次选择,别无选择的我,连原因都不配知道。我心底涌起一股恨:陈狄安,我不会管你大哥的,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医院,外面满地银白。天渐渐亮起来,路灯还没熄,昏黄的人造光笔直射向天际。几片雪花被风吹送,躲进我的眼眶取暖,转眼不见了。想到不久之后,我将在太平间外和陈狄安重逢,想到那些从他身后源源不断涌出的白气——我不在乎你伤不伤心,只要死的不是你就好。 回到家,我把淌泥汤的鞋扔进洗手池,蒙头大睡起来。梦里的影子坐在雪地里,光着两只手团雪球,雪冷,手热,雪都化在她的手里,结成了冰。最后,她手上长出了一只棉花糖形状的水晶球——我惊醒过来,记起今天是大年初七,思芒剧院公布入选新人的日子。 我上楼找影子,发现她在装行李:“你要干什么?” 影子抬起头,两颊是那种特别透明、格外脆弱的红色。很明显,她刚哭过。 她失败过六次,这次是第七次,她终于承认自己不行,犯不着诋毁命运——突然,一个笑容在她脸上炸开,我的心一颤,这些年了,她一点没变。 我上去抱着她:“我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影子推开我,继续装箱子,“萧觅刚通知我,明天才开发布会。” 我看她装完当季服装,又开始装春秋的卫衣和夏天的短袖:“你要去哪?” “思芒啊,今天签约,明天开始封闭创作。” ——“什么?” “我被选上了,我要见到英木黎了。”影子奇怪地看着我,“你不是说你知道吗?” “选上了?萧觅说你选上了?”我简直像在做梦。 “嗯,她给我三个月时间写剧本,半年后剧目在思芒公演。” “她还说什么了?” “等我的剧目公演,一样搞‘提前离场’,不同的是,第二个新人由我来选。” 这分明是把英木黎架空了,我问她:“萧觅有没有提到英木黎?” 影子愣了一下,摇摇头。 “你听我说,萧觅正在和英木黎闹分家。”我握住她的手,让她冷静下来,“和曲谱的恋情曝光后,英木黎没脸再大张旗鼓地怀念麦芒,所以思芒剧院对她已经没用了,一旦分家,她第一个就会把剧院剥离出去。就现在的情形看,萧觅让你过去,是为了让你接手英木黎的工作。” “阿真,我比你更了解英木黎,她不会爱上曲谱,也不会和萧觅分家。”影子把箱子立起来,拖到门口,又回到书房里,把辞职信装进信封,“我去一趟台里。” 我拦住她:“现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你辞什么职?” “那我也不能脚踏两只船啊!”影子急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英木黎的感情,我从14岁就——” “这样,辞职信先放我这,你去了要是没问题,我帮你交给齐老头。” 影子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了。 临走前,影子从阳台翻出一束手握烟花,从床底掏出一只陶土花盆,跟我说:“不能一起过元宵了,现在放了吧。” 我看着她直发愣:“真要走那么久?” “你干吗啊?”影子哭笑不得,“你当我去跟组不就得了?” 我却感觉自己要失去她了,那是陈狄安离开前,我从未有过的预感。 影子自己拿一支烟花,又递给我一支,郑重其事地说:“烟花燃尽前,手写下的愿望,都会被实现。” 我看她以烟花为笔,在空中飞速写下“英”——“木”——“黎”,这三个字笔画真多啊,晃得我都要流眼泪了。写完最后一捺,影子手劲一大,烟花顺势而灭。她看着手里黑秃秃的一支细竿,脸上的绯红更浓了。 “准备好了吗?”影子轻声问我。 “啊?” “集中精神,我要点了。”可影子老觉得我没准备好,好几次划着了火柴,又扔进花盆里。 我摇摇头,我做不来,点着了也没什么好写的。我站起身,把烟花丢进花盆里,就像扔一只关东煮的签子。我扑到影子的床上,不知道该怎么挽留她。我知道她有才华,有理想,有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我看着她,就像看见一个月前,等待被陈狄安求婚的自己。 隔着卫生间的玻璃,那支烟花在花盆里兀自燃烧起来,发出的光一跳一跳,就像一颗心。那光亮始终不灭,在我梦里跳了好久。久久影子关门出去,我翻个身,听见化雪的声音。 每日阅读更多精彩优质内容,欢迎下载「一个」App。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gn/16631.html
- 上一篇文章: 走错片场了喂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