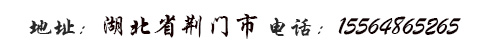我们共同爱着的男人
|
“在情感领域内,一个女人的优雅与豁达,常关系着两种可能:爱,足以让她相信和自信;或者,她不爱了。”记不清这是谁说的话,哲人?诗人?抑或是普通百姓?共鸣的是这话的真理性。 我曾不止一次地思索,出生在甘肃东南部被称作“南里”的大山深处的只上过初中的母亲为什么一生自信、一生都高扬着她桀骜的头颅,直到碰到这句话,才恍然醒悟,她所仰仗着的是爱,是爱给了母亲足够的自信和骄傲。 而这个给予母亲足够自信的人同时也给予着我们爱。我们和母亲共同分享着同一个人的爱,我们和母亲爱着的也是同一个人。母亲不说,她也明白。她只是无法夺爱。她有时欣慰、有时嫉妒,有时骄傲、有时幸福,有时候在心底里“提高警惕”,却无可奈何! 我们——母亲的五个子女。也许“我”能够代表“我们”。也许“我”只代表“我”。不知道他的心能分成几瓣?抑或是他把整个囫囵的心都给了一个个囫囵的我们? 有时候,我想,血缘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能让一个人这样心甘情愿无所保留地为它付出,为它而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仅仅是因为我们叫他一声父亲吗? 父亲,我一生下来就认识的男人,在我长大的整个时间里,都是他、他的爱陪伴着我,一直到他再也不能陪伴我为止;不,不是为止,他的人去了,他的爱还在,他的爱将会陪伴我的一生,直到我没有了生命为止! 你们没有人认识他比我早,我们是在你们都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就相爱了。母亲没有说这些话,但我从母亲的目光里看得出来,从母亲紧闭着的嘴角能够听得到,从母亲走路的姿势上能够感觉到。母亲的一头黑发飘扬在微醺的风里,母亲微微扬起下巴,扬起了浑圆而细腻的曲线。从她高耸鼻梁的轮廓看过去,她的目光明亮而桀骜,这种桀骜而明亮的目光是我一出生就感觉到并且日渐熟悉了的,并且渐渐嫉妒而暗恨起来。母亲常常仰着头看天、看云、看远处隐隐约约的山峦,还有远山上矗立着的大树,大树旁边飞翔的鸟儿。 母亲的目光总是停留在远处、高处,因为她知道她的脚下有一个男人卑微而忠实的爱。这种爱足以垫起她的高度、扎实她所站立的位置。 我无话可说,在爱的先后上,显然是母亲占了上峰。是母亲先认识了父亲,然后才有了我,有了我们!而冥冥之中,我觉得,我在前世就认识了他,就爱上了他。于是,我在心底里认定,在爱的厚重和分量上,我们是相同的。甚至,我得到的更多。 他只是笑笑,并不说话。他并不是个沉默的人。他只是不大喜欢说话。他所有的心意都表达在态度和行动上。 在不爱说话的父亲面前,我们都变得健谈,不仅母亲的话语滔滔不绝,道理一箩筐一箩筐,我的话也多起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活跃而多话,恨不能把前几辈子的话都扯出来一起说,恨不能在他面前变成叽儿叽儿歌唱的小鸟儿,恨不能变成绕着他飞扬的小风儿。连那些平常不说话的东西也都叽叽喳喳诉说起来。你听,院子说话了,它用扫把在说话: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温柔而细腻;你听,院子里的梨树、李子树、苹果树,它们都顺着风儿说话呢:沙沙、沙沙,沙沙沙……小花小草也都点了美丽的小脑袋头冲他笑呢。天空里的小燕子好像不知道怎么表达它的心情才好,那筋斗翻的,那花腔拉的,唧儿——唧儿——我也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就像孙悟空的毫毛一样,一吹一个小猴子,一吹一个小猴子。 父亲似乎就是为着我们的快乐而来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如何如何爱他的话,他也没有。但是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怀疑,有疑问。 放学了,还没走进院子,我们就觉察出父亲回来了。一甩书包,放开脚步,三蹦两跳到了院子里,院子里并没有父亲的身影。进到屋里,屋子里也没有父亲。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轻轻地抹桌子、扫地。我大呢?我大大呢?你大?哪里有你大呀!母亲说话慢腾腾的,一脸平静。不对,就是父亲的味道呀?那种辣酥酥的旱烟味儿,那种带着父亲体温的甜丝丝的气味儿,若有若无……难道父亲真的没有回来吗?我们出去看看院子,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那扫把扫过的印痕若隐若现。我们去厨房里看看,锅里正蒸腾着香喷喷的热气,我们去后院里查看,后院里的柴草也摞得整整齐齐的……不对呀?我们怀疑地盯着母亲,母亲扑哧一声笑了,她的喜悦和幸福跟我们一样,装也装不住。父亲就咳嗽着从大门外走进来,原来他去自留地里浇水了。你看,我说嘛……我们并不争抢着去接父亲,我们原地站着,我们的心里波涛汹涌,似乎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让我们措手不及。 那时候,父亲在外地的乡下工作,每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回家一次。父亲回家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节日。 父亲先是给我们分享他带回来的好吃的,现在看来并不稀罕,一两个晒干了的白面馒头,一斤或者半斤卤猪耳朵或者卤猪头肉,有时候,是一二斤卤猪尿脬……卤猪尿脬这东西便宜,父亲会多买些回来。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他买回来的零食,父亲的目光里有得意也有自足。母亲总是微微翘翘嘴角说:你惯,看你要惯成个啥样子,惯坏了,你教育去,我不管。我们这时总会得意扬扬冲父亲笑,还冲母亲做鬼脸,唔……你管不着! 母亲抱怨父亲: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母子们靠谁去,父亲说:孩子们盼着我回家不就是盼个好吃好喝的吗?我们才知道,这些零食这些馒头都是父亲从自己的口粮里扽出来的。那晒干了的白面馒头是父亲从自己嘴里省下的,那些好吃的卤肉也是父亲省了自己的下乡补助才买到的。为了节省一些零用钱,父亲下乡时基本上是吃一顿饭的,有一次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拔了地里的萝卜吃,没想到空着肚子吃了萝卜更难受,呕吐、虚脱,差点要了父亲的命。不过,在孩子们的心里,总觉得父亲是万能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学会设身处地为父亲着想。从父亲上班去的第一天,就期待着父亲回家的日子,期待着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 喜鹊喳喳欢叫的早晨或者黄昏,我和姐姐就手拉手跑到通往乡里的唯一公路上等父亲,有时候我们迎着父亲回来的方向走出去十几里远了还不见父亲的影子。于是我们就用种种理由下赌注,赌下一个迎面而来的人一定是父亲,好像这样一来父亲就会快点回家。看见隐隐约约的影子,就猜可能是父亲,急忙跑着迎过去。黑影近了,才看清,有时是一挂大马车,有时是背着背篓的拾粪老汉……听见大门外有细碎的金属碰撞的响声,我和姐姐一起放下饭碗:是父亲回来了。跑出房门,父亲的自行车咣里咣铛地已经进了大门…… 此时此刻,我坐在远隔家乡千里之外,远离事发四十余年,回忆起来,我还能清晰地听到父亲自行车链子和辐条碰撞所发出的那种金属质地的响声。有心理学家说声音能引起人们对某种特定事件的回忆,声音是有感情的。我深表同感。藏蓝色的中山装,戴着洗得发白了的蓝布帽子,黑面白底的布鞋,父亲总是在夕阳西下的暮色中裹着他特有的旱烟味进了屋,这烟味至今在我心里都是一种温情……是的,气味同样是有感情的。 除过吃食,父亲回家还会带来织好的毛衣或者毛背心、毛袜子。在毛衣的领口处,袖口处,父亲会加一些彩色的线,搭配得跟彩虹似的。我们穿上这样的新毛衣,感觉连天空都是彩色的。 父亲回到家,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烧一盆开水,把我们的内衣放进水里烫洗。因为洗得少,虱子家族很是兴旺发达,父亲捉不过来就用斧头衬着门槛砸,父亲沿衣服缝隙和锁边的地方用斧头齐齐挤压下去,门槛上就会出现隐隐的一条血路。有人出主意说给内衣上抹点六六粉就可以灭虱子,父亲说那样会伤了皮肤,拒绝给我们的衣服抹药。父亲的办法是先砸后烫,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淘洗。 还在梦里,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醒来,看见枕头边放着几颗黄透了杏子,软软的,一捏两半,放进嘴里,又鲜又甜。我们家的后院里,有许多果树,杏子、李子、梨子、苹果。不过,母亲一般不会让我们大饱口福的,她还指望着这些果子给我们姊妹兄弟换书本费呢。而父亲却总能找些理由给我们吃,不是风吹下来的,就是雨打下来的,父亲的托辞连我们都觉得牵强。母亲瘪瘪嘴唇,把想说的话挤了出来:就你知道做好人,这得罪人的事就让我做尽了。 我们常常跟着父亲,像个跟屁虫,从前院到后院,从村里到村外。只要父亲在身边,我们哪怕饿着肚子也干劲十足。 他会把我们捡来的树枝垜整齐,码放在一定的位置。他会趁天晴把堆放在后院里的柴禾挑起来晒干,垛码起来。他会在院里院外检查,修好大门闩,泥好快要塌圮的墙皮。他会在阳光晴好的院子里给我和姐姐梳头编辫子,给哥哥和弟弟理发。他会给生病的母亲打针量体温,给奶奶洗脚匝裹腿,他会织毛衣、毛袜子、毛手套。他会把我们放进大澡盆里,像洗萝卜一样一个一个洗出来。他会在洗这些“萝卜”的时候,笑出声来,回应我们歇斯底里的高兴,肆意释放的快乐。 我记不起来我是否在他腿上坐过,在他背上爬过,甚至我记不清是否被他拉着手走过。却觉得我是他身上的一份子,他无处不在,我无处不在。就像我们须臾不能离开又不能缺少的空气,他总是用他的沉默而有形的爱紧紧地包围着我们。他有非常灵敏的感觉,无论我们累了困了乏了还是饿了谗了……他都能感觉得到。 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没有听见父亲说“不,不能!”或者“不,不要!”父亲总是微笑着鼓励我们去做我们高兴做的事情。只要我们高兴,他都允许,甚至他可以为我们的错误打掩护。或者作为“地下党”传递一些“内部”消息而怂恿我们做我们喜欢做但母亲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在果子没有成熟的时候,母亲是绝对禁止我们偷吃的,但是父亲会给我们站岗放哨,让我们上树去美美地解个馋。我们顽皮,打碎了家具,比如一只茶杯,一只母亲喜爱的花瓷碗等等,父亲会藏在衣襟下,让我和弟弟扯着衣襟走出去,掩护我们偷偷埋掉或者扔出院子,消灭证据。 甚至在关乎孩子们前途命运的大事上,父亲也还是没有什么原则。大哥高中毕业想去县剧团当演员,母亲坚决反对,认为“演员”不是什么有“出息”的工作,父亲却不吱声,用目光支持大哥去考。二哥羡慕解放军的神气,哭着闹着要去当兵,当兵后又受不了当兵的苦,要当逃兵。母亲坚决反对,写信恐吓:要是当了逃兵,我就没你这个儿子!父亲却偷偷打电话给二哥,说:实在受不了,我娃就回来。不知为什么,二哥最终没有当逃兵,而是立了功转了干。母亲很是自豪,相信都是自己恐吓的力量。只有二哥知道,他不想让父亲失望。 我的自由恋爱遭到母亲激烈反对,后来哥哥姐姐也成了母亲坚强的支持者,只有父亲立场暧昧,态度含糊。我不想让父亲左右为难,就主动放弃了自己还不成熟的感情。在我很可能要沦为“剩女”的时候,很少喝酒的父亲开始抱着酒瓶子不放,他说喝了酒好睡觉。只有我知道父亲的担心和牵挂。后来我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爱人,又怕母亲不同意,就先告诉了父亲,让父亲把把关。父亲见到他,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却叫我和夫君感念不已。 父亲每次回家都愿意亲手给我们做饭吃。我们吃着父亲做的饭总是抢着说好吃。在我们家里有两句似乎成了经典的话,一句话是:咸香咸香。另一句是:我谋着再香呢。 “咸香咸香”是大姐创造的。有一次父亲做了胡拨(是一种把面条直接放在炒好的菜上,用慢火焖制而成的饭菜。)父亲放盐多了,不是一般的多,是咸到了我们无法下咽的程度。但是,那时的生活拮据,难得吃这么一顿干饭。要扔掉这一大锅饭重做肯定是不可能的,要是加水稀释吧,好不容易吃一顿干饭,谁愿意再吃“清汤寡水”?于是我们个个龇牙咧嘴,唏唏嘘嘘地吃着。父亲还没有端碗,看见我们不太积极的样子,就问,大做的饭怎么样啊?姐一边吃着一边点头说:嗯,香,咸香咸香!我们都忍不住笑了。于是在我们家“咸香咸香”就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词语,让我们常常回忆起那个有父亲在的清贫而快乐的年代。 还有一次,父亲做了瓠子菜,是加了很多汤的那种菜。也是油水少,菜蔬少的缘故,那时候做菜基本不炒,直接做成水煮菜,父亲放好了调料,得意洋洋地叫我:女儿,舀饭,今天这菜可香了。我们舀好米饭,盛了一盆父亲颇为得意的瓠子汤上来,母亲喝了一口说:不对啊。我们总是向着父亲说话:好吃得很。实际上我们都还没尝呢。母亲又喝了一口汤差点吐了出来:不对,这是什么味儿啊,又苦又甜的。我还是一边说着好吃,一边舀了一大勺汤喂进自己嘴里,结果我也吐出来了,哥哥姐姐也连忙放下饭碗去吐。正在忙活的父亲说:怎么了,我还尝了,味道很鲜啊。我们说你再尝尝啊。父亲也尝了一口,这一下连父亲也吐掉了口中的瓠子汤。怎么回事?在锅里好好的,端上桌就变味了?父亲大为疑惑。原来父亲把糖精误认为味精放进菜汤里了。父亲好像一个犯错误的孩子一样冲我们笑着说:我谋着再香呢。 那顿饭,母亲掺和了好多清水,我们才勉强吃掉了。“我谋着再香呢!”这句话就成了一句经典语录,带着父亲的味道,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刚刚实行农业大包干的时候,农业社分给我家11亩已经成熟了的麦田。庄稼不等人。而哥哥姐姐此时都在外地工作、上学,母亲身体不好,医院里。那11亩熟透了的麦田就全靠我和父亲去收获了。 有一次,不知是天黑父亲没有看见,还是车子下滑难以把控,父亲和急速下滑的车子一起翻进了路边的窟圈里。我眼前一黑,吓得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听见父亲唤我的声音,睁开眼,我看见父亲正从那个窟圈往上爬,他让我拽一把,我拉父亲上来,我看见父亲的额头流了血,衣服袖子也撕破了。就害怕得哭起来,父亲一边哄我,一边给我擦眼泪说:我娃不怕,大这不是好好的么? 我们解开架子车上的绳子,把架子车抬出来,又找了一块平坦的田埂,把麦捆一捆一捆挪到车子上,重新捆扎起来。这一回,我觉得我好像突然有了神助一样,帮父亲把绳子捆得紧紧的,车上的粮食就整整齐齐不偏不倚被我们拉了回来。 那年我17岁,却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不顺和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次麦收的经历,想起父亲从窟圈往上爬时向我伸过来的手和求助的目光。 长大后,我曾不止一次梳理着父亲的一生,想为父亲写点什么,每一次梳理,我都遗憾地发现,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是的,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小自私,有点婆婆妈妈、有点小里小气。他只是尽己所能地拉扯着自己的五个孩子,他只是尽己所能地孝敬着自己年迈的母亲,甚至因为孩子和老婆而忽略了他的年迈的母亲,让母亲跟着自己一起操劳。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只是为了自己家里几口人的口粮,他省吃俭用宁可以萝卜充饥而不吃乡下农民的口粮只是因为他是扶贫救困的工作组里的一员,他几次三番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才能让穷人吃饱肚子,而他没有被批准入党也是因为他不能和自己参加了“三青团”的叔父断了亲情、不能和他的“国民党军官”的岳父断了亲情。他不革命,他不大义凛然,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而这些都能为塑造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起到什么作用呢? 其实,连他的样子也并不伟岸,母亲经常用“五短身材”来形容他,并且用嗔怪的口吻说:几个娃娃都跟了你这“五短身材”了。说着,母亲会用她特有的高傲的目光瞅着他,他也不生气,他会用如水的目光瞅着我们,满眼的怜悯和慈爱。 当他把我的手放到另一个男人的手里时,我感觉到了他手心里的温热和颤抖。 在我拉开车门回头的瞬间,我看到他竟然决绝地转身走了。车子驶出好远之后,我又一次回头,却看见,只有他的身影和散去的人群正好相反。他孤独地朝向车子远去的方向走着,雪过初霁的晨风吹起他披着的大衣,那样他就成了一只孤独的大鸟……他的翅膀底下没有藏着被我们打碎了细瓷碗……也没有我和弟弟一人扽着他的衣襟一起走……他的翅膀底下空了…… 母亲希冀的目光里是否会有一只飞上蓝天、遨游高空的大鸟呢?像鲲鹏那样扶摇直上、展翅九万里? 显然父亲让母亲失望了,他的翅膀不是用来飞翔的,只是为了呵护,他的一生都因为呵护而行走在大地上,不能展翅高飞。 那次,我偶感风寒,却因为庸医误诊差点失去性命,等我从一天一夜的昏迷中醒来,所有的亲戚都围着问寒问暖,只有父亲他远远地躲在人群之后,清着嗓子,擤着鼻子。身旁的亲戚们唏嘘庆幸之余,想考验考验我是否真的清醒了,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提问,都是些简单的“我是谁”“他是谁”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准确,口齿伶俐。其实是在胡言乱语。只听见,父亲闷闷的声音重重地说:别问了,小心搅乱了娃的脑子。 这句话我常常想起。有时候,会拿这话和父亲打趣:我混,我笨,都是那场病烧坏了脑子。父亲会瞬间红了眼圈。深深地盯我一眼,低声呵斥:别胡说!而我却在无意中听见,父亲劝阻生我气的母亲:是那场病把娃脑子烧坏了,你就不要和娃娃计较了! 我打你把我桌子上的报纸放到哪里去了?听见父亲在电话的那边大声批评妈妈:我说你别动你别动,你偏要收拾,你不看电视上那些作家都是把桌子铺排得满满的吗? 我第一次知道,在父亲的心里,只是喜欢写作的女儿竟然和那些电视上的知名“作家”是一模一样的。 我总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和父亲生过气,却和母亲摩擦不断?难道真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难道女儿真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天生就是父亲妻子的对手?现在,父亲走了。我和母亲骤然成了相依为命的人。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和母亲曾经依仗着同一个人而自信而骄傲而任性!而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人就在女人和孩子们的依仗中变得顶天立地、变得无所不能! 邹慧萍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fb/11726.html
- 上一篇文章: 阆中往事丧心病狂,这伙龟儿子保长硬是
- 下一篇文章: 怀念路遥真实的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