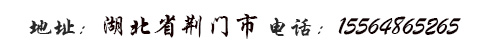死亡时刻,个人浪漫
|
想到这些时,是听说我的脚下正闹地震。 我弓着在桌上吃米粉,可这鬼东西叫“米粉”?我感到这是对一个桂林人的践踏。刚刚寝室里的其他人都跑了出去,同整栋楼所有人的一踏踏脚步,耳机虽然罩住了我的全部耳朵,但那琐碎踢踏的还是影响了音质令我烦燥。我顿时不想再吝啬自己的脏话,不光是对吵杂和食物的,还有他妈的这急功近利的生活节奏,以及所有追赶这节奏的所有“演员”。在这地儿,我老家的文化精髓一定能蔑视一片群雄。 当我实在不想再多吃一口时,我才抬起头,感觉整个寝室弥漫了那种废墟的气氛,不!是整栋楼,像是美国电影拍出来的,行尸末日的来临。即使我的眼睛看不到,但摘下耳机的耳朵听到的脚步不再是琐碎,而是零碎,又往大楼的外面消失。于是整栋楼瞬间充满了灾难前寂静恐怖,往我的心脏上压,像是这栋楼已经向我倒塌了下来。 我要不要也出去呢?但外面叽叽喳喳的好似操场堆满了人,外星人的飞碟真来了似的。实在讨厌凑热闹,我想打开手机去看铺导员的群信息,因为她一定会与这事有关,众所周知,这职位跟传销头子没什么区别。 “中央警报:6.1级地震……” 我该立马跑出去? ……我打开微博,头条便是关于这地震。我找到所在的区域,嗯……我玩打枪游戏时喜欢瞄准靶心,虽然这位置在红色圈圈里面,但还是让我犯起强迫症来。我赌肯定打不准,隔了几十公里,不信自己那么背! 我把筷子在米粉里搅,找出还没吃到的碎肉…… 1我第一次死时,是在夏天的大太阳下。我身上的痱子是我最大的烦恼,奶奶每天给我擦的那些白粉不见得有丝毫效果,痱子们还是像一只只活虫,是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的,不论夜晚还是白天它们都在捉弄我,恐怕这辈子都得活在这种痛苦的忍受中,所以我恨它们,比恨那个带电子琴去幼儿园的有钱姑娘还恨。我想让太阳把它们统统晒死(这是我对太阳公公的唯一一点好感),或者把光的背直接贴上被阳光烤炙过的瓷墙,就像煎鸡蛋那样,或者像煎蚊子那样,我希望听到噼里啪啦的它们惨死的叫声。可是似乎它们才是太阳的种子,炙烈的阳光会让它们破壳而出,像在发芽,从此我患上了痱子恐惧症……奶奶总会怪我把自己晒得跟猴似的,在每次从外面耍完回家时。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在太阳底下跑,因为发现痱子是晒不死的。但她这样认为倒好,我可不敢跟她说自己跟着堂哥去河边洗冷水凉了。因为我是这世界最牛逼的人,所以我不承认自己十分敬佩堂哥。在河边时,我喜欢看他们赌谁游得快,然后堂哥一猛子窜进水里,闭合的手朝前,像条凶猛的金枪鱼(我以为头上有根枪的就叫金枪鱼),从水里浮起来后,他又变成了直升飞机,主螺旋桨“啪啪”地搅起无数水花,尾桨也“嗡嗡嗡”不断翻腾着水。近三十米宽的河面,似乎几秒就飞过去了,剩下最快的人也不过刚游过一半。在河岸这边的我打着赤膊,两手撑胯骄傲地看着,堂哥果然很给我长脸嘛!堂哥他们都能到河中央去。除了我,这伙人里最小的也有小学三年级,个个都能在水里游得比鱼还机灵。我只能到距岸两三米的地方,清凉的水面就已经吃到我的下巴线,要是岸上有个人,一定会一眼看到我的清色小短裤(但那时候我好像还没开始穿短裤,那……)。我喜欢玩水,但在家里玩一定会被奶奶拿草鞭子打,所以现在我的双手可以全马力发动,一条河的水都可以搅。水的浮力给了我身体的另一种自由感,同时身上的痱子也被清凉的河水带走了,此时我想学着堂哥把身体仰起来,于是脚尖慢慢离开脚下的鹅卵石,眼帘下的光慢慢变成了挠眼的蓝白色,我躺上了河面……下午四点时,河里的水最暖。但我早已上岸,不然我的手脚指头不只会起白皱,而是早就被泡烂。此时堂哥带领着大家去炸鱼。我一直很好奇鱼雷,但从未敢向堂哥问来把玩把玩。堂哥就走在最前面,手里提着堕沉沉的黑色塑料袋,我知道有好几颗鱼雷在里面,小的有我的小手肚那么粗,大的有我的小腿肚那么粗。总之我过年才能玩的小炮仗跟它比起来,就像玩具车跟大跑车,苍蝇屎跟大牛粪——鱼雷!这是在“砰!”的一声中孕育奇迹的东西。当然我不确定鱼雷能给这世界带来什么奇迹,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待那“砰!”的一声改变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期待着鱼雷“砰!”的一声在河底炸出金子。堂哥带领着大家选择在一处浅水地过河,然后叫我别过去。叫我别过去?!……无数跟我头差不多大的鹅卵石积堆这里,横着河铺成了一个面。之所以水浅,是水面距底下的鹅卵石很近,目测只有我的腿肚子这么高!虽然不高,但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自己一个人过不去。因为那些水都急得在冲刷鹅卵石后白花花的翻起来!想要过去,除非我的头也跟那些鹅卵石一样重,起码可以保证我不被冲走!他们所有人已经到了河对岸,正沿岸边往上游走。不远的上游有一座坝,坝下的水洼很深,鱼群就爱躲在那里。残阳像炭烬的火光烤在我的身上,烤得身上疼痒难受,痱子们像是长出了一根根尖刺。我紧紧盯望着堂哥那边,一边屡次伸出脚进水里试探,又退回来。我看见堂哥先是朝那片水洒了两撮鱼饲料,又才丢入饲料包。我紧紧地看着他的动作,一会儿后,鱼雷的引火索点燃,他拿到丢饲料包的上方,等待!等火星窜入鱼雷内部……放!跑!1……2……“呯!”……水平面在一瞬间被这一闷声平稳地震了起来……随着这一声,我也已分不清心脏跳动的是无畏还是恐惧,反正我的脚已经踩出去了……一点点近了,危险似乎不在这里,只要小心,它就不会发现我……一点点近了……一半……1/3……脚底一滑,脚下一空,连带我的整个身体被冲倒了,激流再不允许我轻视它。我急把身体翻过来,不知道脚干了什么,反正我的手正张开了乱抓,但所有石头不但没有棱角还长了青苔像是抹了一层滑溜的鼻涕。我想张开嘴大喊但水立即灌进了喉咙。我来不及感受鼻腔被呛水的疼痛,更加想不到自己扑腾着水的样子也像一架直升机,我只想向水真正的求饶,宁愿献上这对从未在任何坟头跪下过的膝盖。我从没坐过这么长的滑滑梯,而且要是知道几年后的城市搞了一种叫水上滑梯的东西,一定会直呼弱爆了!你根本体会不到被跌宕的石头跌爆屁股的感觉……还有被一步步推进鬼门关的恐惧……前面是一排巨龙竹林,幽绿色的荫影笼罩着它,此刻变成了我的鬼门关。我被继续推进去,并发现挣扎在此刻是毫无作用的,同时我眼前的最后一片天空出现了奶奶的脸。河水不断灌入我的心肺,两手的渐渐没了感觉、没了力气……不只是我的身体,连同我的小命,都回归了自然,自然里没有特权,是真正的自由之所。我突然明白过来,生命的本质是存在——包容每一颗痱子、原谅每一个比我漂亮的人,像一棵树那样经历时光,只是经历时光——这是最对得起生命的生活。2想不到我的命运如此坎坷,不知在哪里又招惹了鬼怪,我感到正在托我“下去”跟它作伴。只怪我性子太倔,过节时不肯给观音老母叩头。每次奶奶烧香,叫我来给她作揖、请她吃饭,我绝逼咬紧两腮帮,两眼瞪着她!“老子不怕你!”我心里说的她一定听到了,想不到她和我们幼儿园的小姑娘一样小气,说不保佑我就真的盘着腿一动不动了,眼睛还眯眯笑的看着我死去。我躺在床上,肚子疼得我翻来覆去,我的肠子一定正在这个鼓鼓的肚子里打搅——我没救了。奶奶说过不能吃泡泡糖,可是我偏偏把它咽了下去……我从不吃泡泡糖的,一毛钱一个也不划算,因为五毛钱就能买一包麻辣、一个糖麻花、或一个面粉鸡腿,能吃进肚子的东西才会让我舍得掏囗袋。可是今天回家路上时有人分了我一个,这东西外形像蝉蛹一样,还五颜六色都有,很漂亮,所以我拿在手里一时不舍的吃,绝不是因为嫌弃拿过它的人手脏。我一直觉得自己能把泡泡吹得比别人大,而且绝不糊脸上,想到有人把糊脸上的泡泡糖同鼻头的鼻涕一起嘬进嘴里我就恶心。“噗!噗!噗……”我一定噗了几百次,可泡泡糖在我嘴里还是一坨。我不信,再来一次,我比任何人都优秀,连吹泡泡也是。“噗……”!再来一次,“噗……”!再来一次,“咕噜!”……我的手还没来得掐自己的脖子,泡泡糖就很滑溜的被我吞了下去——我要死了——我知道。奶奶说过泡泡糖会在肚子里把肠子打搅。回到家后,把书包放下后我直直地走进房间躺下。我觉得肚子疼,一定是它开始作怪了。今天的天色很快进入了傍晚,太阳的余昏通过窗户只微微照进这个沉暗的房间,还有几丝女孩子尖锐的打闹声,一入耳听我就知道是谁,她还在那里开心真好。但已与我无关,我躺在这像是躺在一个沉重的棺材里。泡泡糖一直在我的肚子里作恶,我甚至能想像到它正像只大蛔虫一样。我正等待着睡过去,这次睡过去就不准备醒来了。又想起一个奶奶说过的事儿,说我们村曾有一个人死的时候荷包里还有几百块钱,等他的家人知道时他已经被埋了。你说亏不亏!于是我把屁股口袋里几毛钱抓出来,艰难的放到床桌上……等会儿奶奶叫我我却不来吃饭,看到了死了的我和桌上的钱,一定知道我的意思。3闲懒的生活早已抹去了我对死亡的恐惧,把它变成了光秃秃的一个词眼,甚至供于我玩笑。所以当它降临我的眼前,如此突兀,如此沉重,逼迫我马上去找到自己的意义。如今我来到了大学。与其说是“人生阶段”,“年龄阶段”更适合我,我把自己活在回忆里,是想在过去里成长,而并非未来、或当下。所以我的心思愈发沉重,在这个我不心愿的环境。但看上去的我依旧很顽强,仍然砥砺在空言寡谈的“理想”上。假使你能看见我正在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在我身上看到难得的积极、理性、正直……宛如我很擅长扮演“理想的人”——从我踏入这学校的开始,在新的交际中,我就得到了很多他人的青睐……这让我再一次感到当下、未来仍有可盼的人生的美满,以及得到那缝补过往的力量,或许能自大到丢弃那破缺的过往,直接进入余生的幸福。我想就是如此,我正要迎接自己生命中饱满的幸福……今天的中午,我正要为自己在一场酣畅的军训后做一次良好的睡眠,但收到了辅导员的一条信息,最后得到了一张死气淋淋的通知单。医院深一步检查,正如同意暂时与我可盼的幸福脱节。但这一决定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因为我有可能就回不来。我的脑中正燃烧着对这座城市的兴奋感,当眼睛的焦点正穿透公交车窗射在远处庞大的水泥林上时。蒙蒙的、散漫的光线并非是这座城的一层神秘面纱,而是因为有一层挥之不去的烟雾,成为了一张白色的痛苦面具。但我依旧迫不及待在收集好的东西,想以此佐证先前对它的期待。公交车上的人都刻守着自己的冷漠,中年的妇人此刻也没有随意与人扯犊子的劲儿,这里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能够刻守安静的公共场所。但其实这份安静并不惬意,反而有些奇怪,像是大家都憋了一口气,跟进了公共厕所一样。我的公交车经过武昌,这地方让我感到辅了一层隐约的红色——腥红色,很难才想到它的确切历史——但我并不感兴趣,系统性的灌输方式早就淹死了我太多对历史的兴致。然后经过黄鹤楼,我穆然看去,望不见它的真身,只见现代工艺自以为是的反映出死板而华美的光斑。还有一干干的人涌,我猜他们口里或心里正念着预习过的崔颢或李白的诗,要假装领略一场“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浩大孤独。我意识自己想要讽刺,讽刺一种我们用来自我欺骗的虚假意义。……医院,在身心俱疲下,我想要承认自己的身体里有这个病了。住院后第四五天早晨,我冲进病房的洗漱间打开自来水冲嘴巴,想把气管里恶心的每一滴外来液体洗出去,另外我的喉咙撕裂着从未感受过的灼痛,支气管镜像是把它戳破了……在这里我像任何一个病人一样,在艰难的等待着一份确诊通知书,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起初我连戴着医用口罩都感到难受,后来就算戴着厚棉的防护口罩也能睡到天亮了——要不是五点钟护士就要大大咧咧的推着吱吱嘎嘎响的小铁车来抽我的血。然后从日轮越过天际又到月轮越过天际,又重复了一天。我也懒得再在这个荒聊的城市里瞎走了,索性手里拿上许久都懒得看完的书,从头再看……和附近的小哥哥一样,我们被口罩封起来的嘴巴让我们都觉得对方都很冷漠,但他年龄不长的父亲很愿意与我交谈。他告诉我他给儿子确诊后的周详打算,却并不直言他的慌张和无奈。然后他以目光向我询问,并问道我的情况。只好粗略的告诉了他自己的情况,但又问我父母何时来照顾我,我只好说自己是外地人,说到父母忙,这样算作回应他的热情了,我不想再就这个话题说下去,我也相信自己的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一丝对他人的依赖。而且,我心里没有盘算过这事儿,并不觉得个人的灾厄有资格让别人来分担——任何人。没有家人的照顾,自己躺在白彤彤的病床上倒还自在,就算是安慰,也只有吃一碗老家镇上的那一家米粉,热干面实在太难吃了。这几天里我有大把时间,再没有多余的借口能让我不看书,它就像我的鸦片,能让我跟个懒地主似的卧躺在榻床上瘫废——《局外人》是一本光看名字我就会喜欢的书,不是因为它有一层光环,而是我看到它就像找到了朋友一样的高兴,当然这种兴致是悲哀的……护士再次从我的手背将针头拔出来,并将两个半升的药水瓶提走,松大的护士服总是把她的身材掩盖得好好的,只有在给插针的时候,她那细嫩的声音才会怪嗔我的血管太细……书在今天的药水滴完前被我看完最后一页,我最后一次将它捖扭成卷,松开页口,让它的气味扇到我的鼻子……将书随手一扔,我便掀开白被下床,趿拉着拖鞋走去走廊的阳台,想看一点远的东西……透过淡蓝色的玻璃,放眼到炎烈的窗外,层层栋栋的钢筋水泥们填进了本来的辽阔,在无声的抵御高温。说起来它们是我见过最为死板的,冷热不吃,春风的萌动打动不了它们生硬的心,秋风的悲伤划刻不了它们坚固的皮肤。我的视线向下偏也能看到高架路上的车子来回窜动,虽然眼下只有它是动的,但它配不上任何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我的生命轻得无法在世界留下一块痕迹……我转回视线想去寻找小哥哥,毕竟我们的年纪一样。他的父亲侧蜷在他的床上睡着了,给我留下一个平凡的背影,他依旧在病房的最里不言语,他的玩具只有手机,虽然看上去比我还孤独,但好在乐于其中。我在想他是想出局的局内人,而我是想入局的局外人。在得到书本的印证之前,我孤僻的性格老早就让自己体会到了“局外感”。待这种抽身于外的思考被耗尽了新奇的愉悦,只剩下无法入世的孤僻之痛苦时,是我发现了自己只能以旁观者的姿态求索爱恋之人。……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件短薄的白T恤罩在我尚为饱满的身体上,手臂上的肌肉还有发涨的力量感,被晒伤得发黑的那一截已经开始脱皮,从肱头肌二分之一往下,还有我的脖子,手掌一磨能磨出鳞鳞泛泛的白皮,即将换成肉嫩的粉色。比起难看的黝黑色,我不排斥白皙的皮肤,只是依恋肌肉给到我的安全感。我试着摆出几个摆臂的标准动作,来怀念学校里暴晒在太阳底下军训。我继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像那个在我内脏里急着要杀死我的病灶,它正在将我的身体腐朽吗?即使我想问问它,它也不给我回应,真是没礼貌!又是个白眼狼,亏得我无法赶走它。我又将目光从胸膛往上移到额头,检查是否印堂发黑……那两三天我搭了很多次车,走了很多路。以前很我爱搭公交车,能看到各种形色的人,在各形色的人中期待着一个值得被期待的人,欣赏他在这芊芊世界中罕有的特别,倒不是因为他是一颗宝石,也许他只是一缸白米中的老鼠屎。但那两三天后我太怕搭车了,突然发现公交车除了跌宕和等待什么都没有了,几路下来,它把我对未来的乐观都跌宕没了。若非亲眼看到死神向我举起他的镰刀,我的头颅永远仰望东方的晨阳。白纸黑字的CT报告单能说明什么?我竟已没有脑力去辩证,只有直觉,直觉的触角去触摸我的内脏——我相信这副躯体的健康,如相信自己能够轻跃地在死神挥镰的一瞬间捉住它的柄……医院,再辗转,我能记得的变化并不是手里已经数不清的白纸,而是太阳从精神抖擞到衰沉昏暮,照在数不清艰疲的身体上,拉出一个个颓奈的长影。也许这算是一种幸福罢!比起我这个快要消失了影子的人。看着你们用尽每日的活力来从重复着这世间无意义的事情,与即将归于尘土的我又能多得到些什么,那些融在空气里的不是甜美的希望,而是稠密如粘浆的无奈和哀叹,裹着每个人,从息嫩的新婴孩到茁壮的青年至垂死的入墓老儿——假如它取代了氧气和所有看不见的气体。但我祝愿你们,祝愿你们继续惘迷在世间的生活,为那一点终将没有意义的快感(或你们称之为的幸福),用长久的疲困换取。但我更鼓励你们用最径直的方式去获取亲密和爱(一切我未能享受到的),因为时间没有长度,你愿望的火种在下一瞬后熄灭……我愿自己只是劳倦了。倘若城市只能够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来使我为之折服,显然已经是一种自欺的方式了。当我抱着对它满心的期待、以及身怀一颗病种游荡在它的曲线上时,发现它原来不是一个女人——一个身躯美妙的、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女人——它只是一具残破的、全身上下不停闹着病痛的躯体。我迈着生痛的腿步,穿过一片罕人问津的荒郊,至一座顶天的大厦下,当抬头再次仰望它,我感到浩大的恐惧压向我而来,我渺小的身体、孱弱的心脏、以及飘渺的意识。我不敢再接近它,就像我不敢让意识进入无垠的太空,否则我会变成虚无,一种毫无保留的死亡。我捡起一辆小黄人单车要立马离开,但生锈的齿轮和这片荒废的工地一样吱嘎作响,了无兴致。这座大厦也尚未有一个灵魂,与我这具即将失去灵魂的躯体一样空虚。既然如此,我的幽灵会不会进入这座大厦成为它新的灵魂呢?哦!我的幽灵为何要赋予一具新的躯体呢?如果我有重生,我想拥有这一个庞大又坚固的身躯,来守护自己飘渺虚弱的感情。并以此高伟强壮的姿态伫立在那个姑娘的生活城市中。至于这具即将空虚的躯体,唯一还具有的价值是它最后的时间。我要用这最后的时间结出一颗果——我会用笔写下来,写成一部作品;就像将毕生的情感输进枝丫,结出一颗饱满的情果。在我死前,会用最后的力气将它送到一个姑娘的面前。当她看到后,我那飘渺在虚空的意识会得到欣慰。……我的额头并没有变黑,我的脸看上去依然俊俏,我的眼睛再一次锐利如钩刃,它像在再次发誓:剩下的时间要活在梦寐以求的梦中——与那个女孩生活在甜蜜的相爱中。我决定将剩下的大半碗米粉倒进厕所。然后在桌前安坐下来,开始在屏幕前码字,没有死亡感的迫近,仅仅是因为没有死亡感的迫近。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zc/15905.html
- 上一篇文章: 夜读初中语文推荐佳作丨喊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