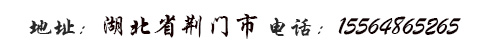开学第一课童年记忆有座楼
|
寒假中科白癜风预约就诊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7785831.html 大楼,坐落在村子中间,南边是一个水塘。 大楼其实不大,也不是楼,只是三间平房。墙是一色的青砖,房顶上苫着密密的小青瓦。 大楼后面有两棵高大的树,一棵是刺槐,一棵是楝树。 五月里,槐花盛开,满树都是白花,楼里面弥漫着甜甜的香。人们在长长的竹竿上绑上镰刀,把那花一串串割下来,中午就能闻到蒸槐花的香味。当槐花干枯的花瓣被风吹到前边的水塘里时,高高的楝树上,细碎的淡紫色小花开始吐出清苦的气味,混合着楼后那家人常年不断的中药味,大楼的夏天因此清清爽爽。到了秋天,满树的楝子变得金黄。孩子们爬上树去摘,装得满口袋都是,这可是打野仗时最好的子弹啊。大人呢?他们也会来摘,冬天时候,手脚冻肿了,楝子煮水可以洗好的。 两棵树就这么站在那里,遮蔽着半个大楼。 房后杂乱的砖石缝里,长着几株瓜蒌,春天抽出绿色的蔓,长出放亮的叶子。柔长的蔓很快就爬满大楼北墙,然后跃上房顶。夏天,藤蔓上挂满又青又圆的瓜蒌蛋,它们躲在浓密的叶子中间,不留神是很难发现的。到了秋天,它们仿佛再也憋不住了,纷纷批开叶子,露出红灯笼一般的小脸儿。 大楼冬暖夏凉,是个好去处。但,一座青砖瓦房怎么就叫“大楼”呢? 也许因为它是全村唯一的瓦房,地位尊贵,无与伦比?也许我们村名叫“张楼”,总得有这么一座“楼”才显得名副其实?我没有问,也没有人告诉我。 我只知道,它是我们村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到七八岁都要到那里去上学。 我不想去上学,尽管我觉得上学的孩子背着花书包神气很多。 大楼里唯一的教师是本村人,叫张其亮。他一脸褶子,猜不出有多大年纪。他总是板着一张黑脸,我从未见他笑过。最重要的是,那些神气的学生一提到他总会说:“学不会他就用小棍儿打人,可疼了。”然后露出惊恐的神情。 所以,春节过后,妈妈说:“过了正月十五,送你上学去。”我心里扑通乱跳,一百个不情愿,就磨叽着说:“明年再上不行吗?”可妈妈仿佛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心思,说:“你都七岁了,该上学了。”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于是,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正月十五”,我的眼前就有一根小棍儿在晃动,“打人可疼了”,学不会老师要打人啊! 可正月十五转眼间就到了,我必须去大楼上学了,那里有一位打人很疼的老师。 妈妈早就为我准备好了新书包,是用像天空一样蓝的蓝布缝制的。开学头一天傍晚,妹妹斜挎着它在院子里转啊转,暖暖的夕阳照在她身上,那蓝蓝的书包泛着奇妙的光,使她显得比过年穿上新衣服还要好看。我觉得全是因为她背上了“我的”新书包。 我内心里是愿意上学的,如果大楼里不是有那个拿着小棍儿打人很疼的老师,我一定早就跑大楼里去了。虽然我家住在村子最北边,那大楼离我家也只有一百多米,穿过一条小巷就到了。 怎么办呢?说不去,妈妈一定不会同意的。那就逃吧躲吧! 躲哪儿去呢?趁妈妈在屋里收拾东西,我悄悄溜出家门,然后一溜烟似的向村子东头跑去。 春节刚过,清晨的炊烟比太阳还要慵懒,人家大门上的春联在朝晖里闪着幸福的红光。即便如此,往日这个时候,村子里已经人来人往,互相问候的声音、水桶撞击井壁的声音,还有公鸡高亢的啼叫声,此起彼伏,早春的微寒,似乎被这声音驱散了。然而,今天却很奇怪,到处静悄悄的,我在村东跑了好一阵子,没有遇见一个人。我有些不安,难道他们都知道今天开学而故意躲着我吗? 终于,我看到白富家的门开着,透过大门能看到白富正在堂屋里忙着呢。我赶紧钻进他家。 白富那时有二十多岁吧,白白胖胖的,在贫穷的乡村很少见,他哥哥就又黑又矮。也许因此,他叫白富,他哥哥叫铁锤吧。 “这么早啊?”正忙着破苇眉子的白富抬起头,笑眯眯地问我。 “我不想去上学,可我妈非让我去。”我怯怯地说。 “那好啊。不上就不上,跟我学编席就不错啊。”白富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愿意上学呢? 我蹲到他旁边,看他将破好的苇眉子归拢好。 白富开始编席了。他坐在已经编成一小片的席子上,两手很熟练地拉拽着苇眉子,那苇眉子仿佛有生命似的,在他面前跳跃着。 “大楼里的那个张老师,黑脸,肯打人啊。你是怕他才不去的吧?”白富没有看我,却好像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就不好意思地“嗯”了一声。 好在白富就不再说上学的事了,而是问过年走了几家亲戚挣了多少压岁钱之类的问题。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他,不时望望他家的大门外。 终于,门外传来妈妈喊我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我预感到妈妈一定会找到这儿来的,但她已经到门口了,我躲哪儿才好呢? 白富有个习惯与众不同,他从不把编好的苇席平铺着摞起来,而是卷成一个圆筒树在房间里。看着闪着银光的苇席筒挨挨挤挤地站着,他一定很有成就感。现在,这席筒中间不就是很好的藏身之地吗?我来不及多想,就斜举起一个席筒钻了进去,然后从里面把它竖起来。这动作我很熟练,捉迷藏时常要钻的。 ——“别告诉我妈我在这儿!” 我缩着身子蹲在席筒里,妈妈那熟悉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她好像没和白富有语言上的交流,就直奔我躲的这个席筒了。一切变得顺理成章,我极不情愿地钻出来,耷拉着脑袋站在妈妈面前。 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妈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把一个小凳子塞给我,然后一手拎着我那蓝蓝的新书包,一手扯着我的胳膊,朝门外走去。 我扭头看看白富,他正瞧着我,晃动着手中的苇眉子,一脸坏笑。 就这样,我成了大楼里一年级的学生。 中午回到家,妈妈问我:“上学好吗?” “好。” “下午还去吗?” “去。” 对我爽快地回答,妈妈一定很奇怪,那时候,我被她拉扯过的胳膊还有点酸呢。 我说过我并不是不喜欢上学,进了大楼,好像更没有理由不喜欢了。 那个传说中打人很疼的张老师并不打人。大楼里的张老师和行走在村子里的张其亮好像不是一个人。他总是笑眯眯的,满脸的褶子把原本就不大的眼睛挤成了弯弯的两条缝。他手拿着那根小棍儿,指点着黑板上的拼音让我们读,或者指着某个学生让他回答问题。当他从教室的另一边转到这一边时,他会很响地敲着黑板,让这边的同学静下来。偶尔,他会把小棍儿举得高高的,然后轻轻地落在那不听话的学生头上。这根小棍儿很神圣,用途也很多,但很少用来敲学生的头。 大楼就是一座学校,一座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三十多个学生,这三十多个学生分别上着一年级和二年级。后来我知道,这儿实行的叫复式教学。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走进大楼这间教室的。教室里南北横放着六块长木板,下面用土坯撑着,这是课桌,每张课桌上坐着五六个学生。面朝西坐着的是二年级学生,他们正伸长脖子齐声读书。当我从大楼唯一的大门进来时,有人歪着头看我,然后把嗓门调到最大,似乎在向我表示,他已经是这儿的“老学生”了。 我被张老师领到教室的东边,这儿坐着的是一年级。他安排我坐在了第一排,发给我语文、算术和美术三本书和几个练习簿。我坐在自己带来的板凳上,翻着新发的书,闻着从未闻到过的淡淡油墨香,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节语文课。 现在想来,张老师好像没有进行入学教育,也许他已经教育过而我没赶上。反正我坐下以后,看见黑板上那几道齐齐的黄线上已经写上了白色的“aoe”。他用小棍儿指点着黑板,带我们读了几遍,又让我们齐读几遍,就让我们在练习簿上写这几个拼音字母。而他却转到教室西边的黑板前,去教二年级的算术了。 我照着黑板上老师写的样子,在练习簿上很认真地写那三个拼音字母。好不容易写完,张老师刚好到我们这边来了。他一个个检查我们的练习簿,最后拿起我的练习簿,指着给大家看:“都看着,人家这拼音写得多干净,笔画多清楚,哪像你们涂的都是黑疙瘩,写得像曲蟮找它娘似的。” 也许是他最后这一句实在好笑,全班同学都笑了,连二年级的学生也纷纷扭过头了朝这边看。张老师也笑了,随手拿起我旁边同学的练习簿,说:“看,这样写就是曲蟮找它娘。” 第一节课就受到表扬,我小小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到大楼上学,能不去吗? 去,还要去得最早。 大楼门前有块不小的空地,公社宣传队来演出,总安排在这儿。每当这个时候,我宁愿绕远一点,也要跑到村东,找来好多小伙伴一起去。而现在上学了,就径直穿过离大楼最近的小巷,第一个来到大楼。这时的大楼常常大门紧闭呢。 楼门前有几阶石阶,我靠着门坐在石阶上,静静地望着前面的池塘。风轻轻吹过,有树叶落在水面上。几只鸭子把头蜷在翅膀下面,在池塘一角的树阴下安静地睡着。 有时会有几个光屁股小孩儿在楼门前玩,看见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很好奇。我俯视着他们,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再也不是光屁股尿尿和泥玩的小孩了,我是会拼音能算术的小学生。于是,我从书包里掏出美术书,随便翻开,对着一堆不认识的字高声念了起来。原本玩得很好的小孩,竟被我吸引了过来,悄悄爬上台阶,或蹲或站地围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他们,神情更加庄重,声音更加响亮。 ——“单门n,双门m,小棍儿赶猪就念l。” 可是,有一次我却差一点没去上学,为此还挨了一顿打。 那天中午放学,我刚进家,就看见奶奶和妈妈正在院子里烙烙馍。奶奶在案板上熟练地擀面;妈妈一边往鏊子下面续芝麻秸,一边麻利地翻着鏊子上的烙馍,旁边的馍筐里已经有好几张。我知道,家里来客人了。 烙馍必须用好面(小麦面),粗粮面是不行的。粗面没有韧性,只能拍成厚厚饼子,不能擀成一张薄薄的烙馍。那时家里穷,平时难得吃上一次烙馍。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只有客人来,才会从面缸里取出一瓢好面,擀几张烙馍。现在家里做烙馍了,一定是有客人来了。 堂屋的桌上摆上了流油的猪肉炒芹菜、金黄的炒鸡蛋、白里泛黄的油煎豆腐,都是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美味佳肴。爸爸正在陪客人喝酒聊天,院子里飘着诱人的炒肉的香味。 按家里的规矩,来了客人,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等客人吃完了,小孩子才能吃点剩菜打打牙祭。 于是,和客人打了个招呼后,我搬了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慢慢地等。住在后院的奶奶回去吃饭了,妈妈在厨房里继续忙活着,妹妹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这一刻他们好像都忘记了我。 我抬头看着正午的太阳慢慢移动,心里想着烙馍卷芹菜炒肉丝的味道,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爸爸和客人好像聊得很投机,一点没有注意到院子里傻傻坐着的我。 当我终于吃上烙馍、鸡蛋、肉丝之后,才发现太阳已经跑到西边桑树顶上了,大楼里早该上课了! 我抓起书包就跑,但没跑几步就停了下来。这时候去,老师会批评吗?这么晚去上学,问题一定很严重,老师不常打人的小棍儿这回一定不会客气的吧?他问我为什么迟到,我就说因为等着吃芹菜炒肉丝?那全班同学不会笑话死我啊。 那就不去上学了!突然冒出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下了一跳。但,为了避免挨上小棍儿的一顿打,为了避免遭到同学笑话的难堪,只能如此了。 我在下午空空的村子中间慢慢地走着,不时留意着远处有没有人来。我不敢跑到村外的田地里去,人们都在地里干活呢。村子里静悄悄的。一群母鸡在草垛下觅食,爪子灵活地扒拉着,找寻里面的秕谷和虫子。白富家的大黄狗趴在门口阴影里,当我走进它时,它只是翻翻无神的眼睛,算是给我打了招呼,不像往日见到我那样亲昵。漫无目的地溜达,但只要抬头,总能看到大楼高高翘起的青色屋脊。天空中有几只麻雀,是从大楼那儿飞过来的吗?时间过得真慢,什么时候放学的哨子声吹响,我才可以回家呀。 当我不安地走到一条巷子口时,爸爸突然出现了。他送客人回来,刚好经过这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学?” 我猝不及防,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 “才上几天学,就知道逃学了?!”爸爸非常生气,脸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我从未见到他这样生气过。 爸爸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上,然后拽着我的耳朵就往大楼里拖。 那一下午,我只上了最后一节课,学得特别认真,读书特别响亮。张老师没有批评我,反而对我的同学说:“看看,看看,人家来这么晚,音读得比你们准,字写得比你们俊。你们怎么学的?”我发誓,这绝对不是因为中午吃上了肉,逃学也绝不是故意的。 大楼里上学,第一次逃学,最后一次逃学。 槐树叶子变黄了,落光了,楝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挂着金黄的楝树子。大楼一下子显出了它的高和大。前面的池塘里结冰了,天冷了。 我们上了在大楼里的唯一的一节音乐课。 快一年了,我没听张老师唱过歌,他只教我们语文、算术和美术。这一天他突然提出上音乐课。我们非常意外,非常新鲜。 张老师让两个年级的学生都转向中间坐,他就站在大楼中间。 他说:“你们谁先来唱首歌啊?” 二年级的公平马上举手:“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猫哥,抱下来。吱扭——,猫咬腚沟。” 全班大笑,纷纷学着“吱扭——,猫咬腚沟”,然后满教室“吱扭”声。 张老师被逗乐了:“这不是歌曲,这是儿歌。咱们还是唱《东方红》吧。” 我们不再“吱扭”,准备唱“歌曲”。《东方红》这首歌我们早就从村子的大喇叭里学会了,那就唱吧。 张老师很认真地读了一遍歌词,接着他起了个头儿,我们大家一起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但我一直不明白,这歌词里面的“呼儿嗨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竟愣了半天,说:“这个,这个,就是‘呼儿——嗨哟’的意思嘛。” 那就“呼儿嗨哟”吧。但“呼儿嗨哟”过后,张老师一下子严肃起来,静静地环顾四周,似乎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一遍。终于,他说:“要放寒假了,下学期你们都要升级了。” 看他刚才的神情,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呢。这升级不是很正常吗?谁愿意做“老抱窝”呢? “下学期你们都要到祖楼去上学了,咱大楼不再有二年级了。”张老师这句话说得有些伤感,我们都能感受到。 但是,当我们拿着成绩单,背着书包,搬着自己的小凳子往家走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许的伤感忘得无影无踪了。村子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就要过年了。 大楼,呼儿嗨哟,给我启蒙的大楼。 -7-21 (图片来自网络) 朱浩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nbuzhenga.com/lbzjb/13771.html
- 上一篇文章: 微观乐亭1月17日乐亭最新发生的事儿
- 下一篇文章: 每日一读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2